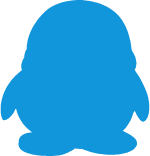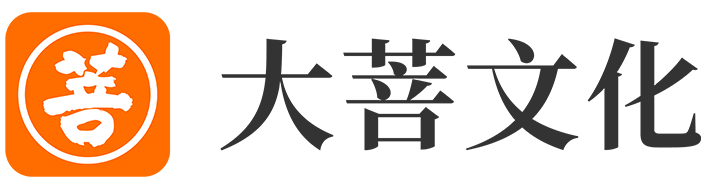
彌勒內院
僧難解除之后,慈航禪師開始新一輪的弘法事業,忙于各種的講經活動。
他在臺北法華寺講過《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在十普寺講《地藏菩薩本愿經》,這些活動都是定期的大眾演講。
慈航禪師總以講經非其本愿,他更希望能夠有個固定場所興辦教育,通過講學培育新人。
因為無處安身,許多大陸避難而來的僧青年顛沛流離,生活陷于困頓。一心關注僧青年生活的慈航禪師對此深感痛心,寢食難安。1949 年除夕夜,于靜修院大家圍爐吃年夜飯的時候,慈航禪師忽然停住筷子,再也不肯入食。
眾人詢問原因,慈航禪師仰起頭感嘆地說:“今晚我在這里吃得這么豐富的菜,不知他們此時過的是什么生活?吃的是什么?”
原來他心里還掛念那些大陸來臺的僧青年們。
說到這里,他是眼淚直流。“你們發心趕快想辦法,建一所簡單的僧舍,供給大陸來的僧青年集合在一起,安心求法,即功德無量!”
眾人深受感動,隨口答應說:“好!請師父放心,別再傷心。請您安心吃飯,過了年我們一定會滿師父的愿望,讓你們師生共住一堂。”
聽到這樣的許諾,慈航禪師才轉悲為喜,高興地用餐了。
由此,才有了彌勒內院的建設。
彌勒內院可以說是在慈航禪師偉大的精神的感召下而成就的,據當家師說,內院的建筑費除傾靜修院常住多年的積蓄及其私人所存的一些首飾賣光當光外,還要借款。
但建筑內院的消息,卻給當時的青年學僧們帶來的是無盡的喜悅,就如沙漠中見綠洲,沉淪中攀到救生艇!
1950年秋,彌勒內院落成了。社會各界人士,佛教四眾弟子紛紛前來祝賀,匾額對聯,琳瑯滿目。
落成典禮上,大眾禮佛道賀完畢之后,就由慈航禪師升座演講。
他動情地談到建立彌勒內院的宗旨以及定名“彌勒內院”的意義說:
這所房子,定名為彌勒內院的理由,約有以下六個意義:
(1)今日的時代是何時代?這是人人腦筋里應該認清的問題——是人類互相殘殺的時代。……現在,我們知道瞋是這個事實的根。若要克服這個敵人,拔除這個根本,唯有慈悲,才有辦法。彌勒菩薩(稱為慈氏)在兜率陀內院宣說慈悲,度眾生于苦海;所以,這所房子定名為彌勒內院。就是要發揚彌勒菩薩大慈大悲的精神,闡述彌勒菩薩大慈大悲的教理,希望每個眾生,都來學彌勒菩薩。如是由小向大,以及由近而遠的方法,以便消弭人類互相殘殺的根源。所謂“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這是定名為彌勒內院的第一個意義。
(2)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為什么會你爭我奪?為什么會你不喜歡我,我不喜歡你?你不喜歡他,他又不喜歡你呢?詳細研究這個病根,是在有“我”。……所以世界上擾亂不堪,其病根就在此。要對治這個病癥,還是要修彌勒菩薩的唯識觀才能收效。要知道弛一方面教化眾生,一方面自己修行,用唯識來觀察一切東西,都是心識所變的。既然是識所變的,自然就無“我”,“我”既無,也就無有“我所”了。既無“我”、無“我所”,哪里還有什么斗爭呢?……這是定名為彌勒內院的第二個意義。
(3)兜率陀天的內院,是彌勒菩薩住在里面,教化眾生無“我”、無“我所”、萬法唯識的道理的。現在要把彌勒菩薩大慈大悲的精神及無我、無我所的唯識道理,由臺灣傳布到中國大陸,由大陸傳布到全世界,使人人都能夠信受奉行。這是定名為彌勒內院的第三個意義。
(4)在佛經上講,每一個世界,一定有個佛在那里說法教化眾生。釋尊的教法: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現在是末法時期,還有八千年,那時經典也就沒有了!彌勒菩薩就來此世界龍華三會說法。可以說彌勒菩薩是候補釋迦牟尼佛之職位而傳行教化的,現在要預備龍華三會,普度眾生。這是定名為彌勒內院的第四個意義。
(5)有人問我修什么宗?我答:“人家說我修什么宗,就是修什么宗。”具體地說,我修的是菩提宗,因為十宗都是菩提。科學是注意系統法的,例如天文、地理等;科學又注重分析法,例如原子、電子等;唯識的教理,也是注重系統法和分析法的。不過科學制造飛機洋船等,有利也有弊;飛機洋船乘人載貨是有利的,而打仗殺人就有弊了。唯識的教理是有科學之利,而無科學之弊的;我們要以唯識學來補救科學之不足。這是定名為彌勒內院的第五個意義。
(6)每一個宗派都有他的傳承,唯識宗是由釋迦世尊傳彌勒菩薩,由彌勒菩薩傳無著菩薩,由無著菩薩傳世親菩薩,由世親菩薩傳護法菩薩,由護法菩薩傳戒賢論師,由戒賢論師傳玄奘法師,由玄奘法師傳窺基法師,由窺基法師流傳到現在太虛大師。本人三十歲以前,從度厄法師是修凈土的,后來又入禪宗,迄今就研究唯識,得益于太虛大師的地方很多。我常說:“以佛心為己心,以師志為己志。”我只希望生生世世講經說法,不問生在那一方,盡虛空、遍法界,我都可以的。地藏菩薩發愿:“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我的愿力是:“地獄已空,我也不成佛;眾生度盡,我也不證菩提。”其實人人現在就是佛,為什么還要另外成一個什么佛呢?佛說:“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不過被妄想所迷,自己不認識自己而已!”所謂“識得眾生,方成佛界”。我不想生天,不想做阿羅漢,不想證辟支佛,只要講經說法;成佛不成佛,我是不問的。……本院供的佛,是釋迦世尊、彌勒菩薩、太虛大師,是表示三位一體;本人即在這彌勒內院代表三位闡揚唯識教理。這是定名為彌勒內院的第六個意義。
彌勒內院又是菩薩學處,又是太虛大師的紀念堂。今天舉行落成典禮了,這個功德要謝謝靜修院的達心和玄光兩位住持。這院是一所法師公共寮,從明天起,宣講《太虛大師全書》,學生來者不拒,去者不留,不另外招生。《太虛大師全書》有百余種,現在已出版至十三冊,此外尚有大師《年譜》兩冊。我們在院內講唯識,在外院勸人念阿彌陀佛,這是希望大家“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今天承蒙諸位大德居士的光臨,非常地感激,希望諸位多多指教,以期大家發菩薩心,來菩薩學處,學做菩薩。將來佛法得以宏揚世界,才不辜負這彌勒內院的成立,和彌勒菩薩升座舉行紀念的意義。
對于慈航禪師來說,建立彌勒內院除了安僧住眾外,它實際上還有另一層意義:繼承和發揚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精神,為佛教改革培育新的人才。故而彌勒內院建成后,慈航禪師就將彌勒內院稱為太虛大師紀念堂,而且把太虛大師的遺像供奉于彌勒像前,以此來紀念太虛大師——也以此再次表達自己作為太虛大師弟子的心跡。

寶島臺灣汐止彌勒內院
?
落成之后,自立法師和妙峰法師奉命前來幫忙,散在各處的同學也就接踵而來。
老人看見一批批的青年學子提著行囊,像游子歸家、奔投慈母的懷抱一樣,他那時的喜悅是無法形容的:“啊!都來了?好!好!洗洗面……妙峰法師,告訴廚房多弄幾個人的飯。”
彌勒內院建成之后,青年學僧們總算有了一個較為安定的地方。唯慈法師抒情地描述了學僧們此刻的心情說:
逃難抵臺的出家青年,幾乎完全以內院為向往的中心,當內院的建筑完成不久, 散居在中壢、新竹、基隆等出家青年,十之七八都陸陸續續地集合到慈航法師的身邊,三十八年(1949)秋冬之季的苦難生涯,此時已成過去,現在自己有了安身之處,慈老的心境,就像雨后太空,陰云散盡,一片晴朗;親近慈老的同學,此刻也像水上的漂萍,忽然靠近泥土生根了,不再四散漂流,心里有了落實的安全感,讀書的興趣自然提高,彌勒內院前后的路邊,微斜的山坡上,旭陽初上,或夕陽西下之時,便聽到瑯瑯的讀書聲了。
自彌勒內院建成開始,這里就成為慈航禪師在臺教學的中心,漸漸匯集了大量的僧青年,朝氣蓬勃,萬象更新。
彌勒內院作為當時臺灣為數不多的佛學院,可謂僧青年心目中的圣地。臺灣著名小說家陳若曦的名作、佛教小說《慧心蓮》中即提及彌勒內院。小說主人公承依出家后被師父送到汐止彌勒內院,主修英語,兼修佛教史。
有了彌勒內院,慈航禪師笑了!像彌勒菩薩那樣笑了! 因為,已達到他理想中的悲愿!
上一篇
下一篇
《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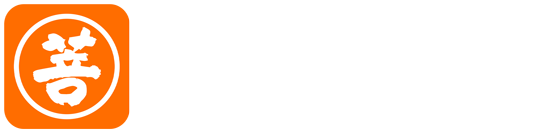

 我要投稿
我要投稿 返回大菩文化首頁
返回大菩文化首頁 返回資訊頻道
返回資訊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