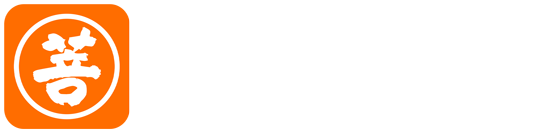為官吳縣的一個丙申六月,宏道撇下心頭政務,想來陰澄湖走走。在《陰澄湖》篇寫道:“與顧靖甫放舟湖心,被襟解帶,涼風颯然而至。西望山色,出城頭如髻,不知身之為吏也。”忙中偷閑一游,覽興舒發,于眼前湖光山色之中,竟然忘卻了自己身披官職。讀者也可借此以文識人,宏道有其任情適性之自然瀟灑。然而“少頃,郵者報臺使者至,客主倉皇,未能成禮而別。”誰知突然傳來巡按御史即至的消息,宏道失色,不及作別就焦急回任。轉而成為趣事一樁。
自適性情而深造“自得”之趣,是袁宏道及不少晚明文人的一種特殊處世方式和主要存在方式。于人情世故中固守真心個性、在社會道德規范面前順應個人的情感需求,各任其自為,隨時隨處使精神安適,和所在渾然。所謂“無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自適而不做“適人之適”的“鄉愿”,往往使主體獲得更多的精神自由。人得以成為他自己,并不由某種異己的東西來決定自己,擺脫各種形式的束縛且不沖突于環境,主客觀間的對立消除而實現統一,這往往又增進了精神愉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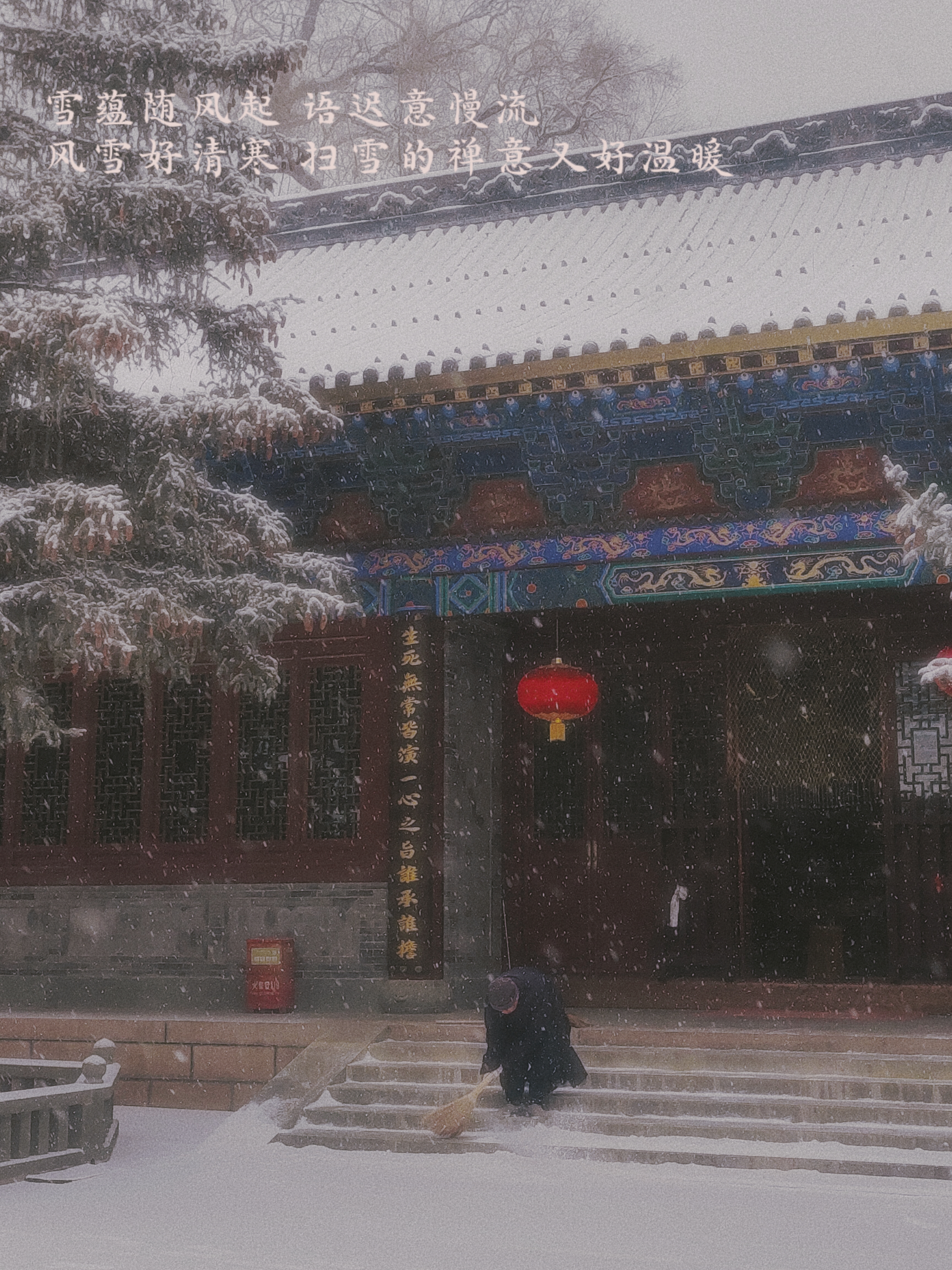
自適的態度系于袁宏道們的一生,猶如潺湲悠澹之水面,自然流動。他們不刻意去塑造高不可攀的人生哲學,精神快樂盡來源于人們可以理解并愿意觸及的日常小景。《與龔惟長先生書》篇講述人間五樂。“篋中藏萬卷書, 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自己做一個有修為的藏書者,而能呼召悉數真友來家中書館坐而論學,由見識極高的人引領,于可近可遠之學問視野中暢話古今,此情此景不失為賞心樂事。 然宏道認為“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 口極世間之譚”才是頭等快活。縱極盡衣食聲色之樂后“家田蕩盡,一身狼狽,朝不謀夕,往來鄉親,恬不知恥”,也不喪其自適之樂。是為真樂也。這種由快樂折射出的人生觀和《敘陳正甫<會心集>》篇表達的趣味觀彼此顧盼。趣之得自學問者尚淺,取自自然者才為深層的情趣。真正的趣味正來源于率心而行,來源于人最無私念雜欲的內心,像“孟子所謂不失赤子,老子所謂能嬰兒”。而后天的學問道理與“趣”卻是矛盾的,入理愈深,去趣愈遠,不受聞見知識纏縛之趣才為發自真心的真趣。宏道之樂趣所以能引起共鳴,是為其“真”也。“真”就是不受外在經驗知識左右的本真狀態。“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而行,是為真人。[1]真人”之“真”輝映于文學上而成“信心而言”“任性而發”的“性靈”之作,把一切創作定位于本然的性情,其理論結果必然是“無聞無識真人”[2]之“真詩”,乃至袁宏道自己的“狂歌”、“浪歌”、“艷歌”之屬,或“謔語居十之七,莊語十之三,均無一字不真”[3]的“真率”之作。袁銑說“中郎公之真文真詩,實本其真性真情真才真識而出之。”[4] 中郎的創作正是其真性情在文學領域的自然延展。其弟中道“間傷俚質”的“疵處”,[5]因充盈著真情實感,難怪“讀而悲之”,令宏道感嘆“大概情至之語,自能感人,是謂真詩,可佳也。”宏道還曾道:“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這種“真”最強調生命的本色存在。
身在官場的宏道不忘時時游憩,脫離吏網之后更是舒逸山水、隨意跋涉。“想求取功名,便仕進;不堪官場惡濁,便辭官;難耐寂寞,又出山。[6]”2006年8月]宏道的仕仕出出都不成其內心的糾結,每一次選擇都是順任自然,不違本愿。他說:“此事只求安心,便作官也好,作農夫也好,做會兒市賈亦好??凡事只平常去,不必驚群動眾,才有絲毫奇特心,便是名根,便是無忌憚小人,反不若好名利人,真實穩安,無遮攔,無委屈,于名利場中作大自在人也。[7]”青年時期的宏道崇尚個性自由,肯定感性追求,也有受禪風所披的疏脫。一種適欲卻不為自己欲望所控制的快樂伴隨著他。“大抵世間只有兩種人,若能屏絕塵慮,妻山侶石,此為最上。如其不然,放情極意,抑其次也。”[8]“吾觀世間學道者有四種人:玩世、出世、諧世、適世。適世一種,其人甚奇,然亦可恨。以為禪,戒行不足;以為儒,口不道堯舜周孔之學,身不行羞惡辭讓之事,于業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務,最天下不緊要人。雖于世無所忤違,而賢人君子則斥之唯恐不遠。”[9]宏道最喜此類人,以為自適之極,心竊慕之甚。
與論“趣”時所謂“得之學問者淺”相一致,宏道之“淡”是“擯除理念、淺易,以枯淡出腴潤,本色渾成的風格。” 萬歷三十年后,宏道的詩文由靈機淺豁趨于平允蘊藉,將“淡”的審美范疇引入到了“性靈說”中。萬歷三十二年的《敘咼氏家繩集》中有一番貴“淡”之談:
“蘇子瞻酷嗜陶令詩,貴其淡而適也。凡物釀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靈也。濃者不復薄,甘者不復辛,唯淡也無不可造;無不可造,是文之真變態也。風值水而漪生,日薄山而嵐出,雖有顧、吳,不能設色也,淡之至也。元亮以之。東野、長江欲以人力取淡,刻露之極,遂成寒瘦。香山之率也,玉局之放也,而一累于理,一累于學,故皆望岫焉而卻,其才非不至也,非淡之本色也。”
其中,宏道對郊寒島瘦、白率蘇放詩作的不滿,也“是對自己前期刻露之病的悔悟。” [10]味薄色淺之淡,發揮到宏道這里成為一種非人力、理、學可取得的自然而恬淡的意境。莊子云“淡而無極而眾美從之。”此中“淡”味盡是由自然派生出來的,宏道所慕之“淡”就接近于莊學的本來面目,這種境界唯陶淵明的詩作中得以純正的呈現,凝聚著藝術錘煉的功力,于表面的濃麗更勝一籌。
文品常常是一人本色性靈的獨抒和人生趣味的表達。淡之詩文也正說明著宏道性情的蛻變。尤其是兄宗道去世后,生活上又淡適雍和許多。這種變化使他漸漸遠離濃習粉黛、清歌艷舞,使他認為“心中粗了,可以隱矣。”[11]于是有了客居柳浪的六年。即便不脫宦情,亦保有一份淡泊的情思。
“淡”是“不假雕琢,與真、自然聯系在一起的”,[12]質也同樣本于作者樸素真純自然的精神品格。萬歷三十六年,宏道又作《行素園存稿引》,表達了“質”的審美旨趣。為文者需要經歷一個“刊華而求質,敝精神而學之,博學而詳說”的修養過程,歷經“三變”----“去辭”、“去理”、“去為文之意”,久而久之方能“大其蓄、會諸心”,觸機而發,渙然于胸,胸有所明。表明創作是積蓄了淵博學識后的會心,是擺脫形式上的格套和束縛、去掉華麗辭藻修飾之后的對學識的超越,以一顆自在的創造的心引筆行文,方如“風高響作,月動影隨”般自然而然。宏道早年的自然是“信腕直寄”、胸臆直抒的,而如今求之于“質”的“自然”,則是“經過了復雜的創作過程而后達到的更高層次的自然,是符合藝術創作規律的臻于‘藝術真實’境界上的‘自然。”[13]在真而自然的審美精神上,袁宏道所言的創作主體精神之淡與質是可以合二為一的。[14]

《行》篇說“質,道之干也。”《壽存齋張公七十序》篇說“學道之致,韻是也。”后人并未紹宗顏回之樂和曾點之“童冠詠歌”這樣真正的孔氏學脈,所以臻達玄曠清虛境界的學韻之士常自佛老。至于韻與理的關系,“大都士有韻者,理必入微,而理又不可以得韻。”無心者“理無所托”,自然之韻反而突出,可見韻又是人“情性”“神明”的自然流露,如“稚子之叫跳反擲,醉人之嬉笑怒罵。”從心縱心者,得理后又能斷絕理的束縛,便能使韻全然。韻包含著一種對理的超越,從而進入心靈和精神的自由王國。它可能來自于不經意間的一舉一句,但卻留下了耐人尋味的畫外和言外之思。
早在萬歷二十八年,袁宏道就于官居北京的閑暇研究插花藝術,用心琢磨插花的花目、器具、花枝的繁瘦高低疏密,力求花與器具“意態天然”等等,著成《瓶史引》,正是其此時雅韻觀念的一種詩學表述。“夫幽人韻士,屏絕聲色,其嗜好不得不鐘于山水花竹。”“夫幽人韻士者,處于不爭之地,而以一切讓天下之人者也。”宏道尚韻,既含對“理”的掙脫,又講對名利的超越,與真正的世俗總保持著一定的心理距離。
宏道的一生,是真、趣、適、淡、韻、質的一生,是審美情操和人生情致不可多得的一生。佛學滋養著袁宏道的人之性靈與文之性靈,參佛修佛,擷錄經典,佛學創作……佛學,影響著他的人生價值觀,和他的生命、性情發生著因緣,這份因緣使我們視角里的袁宏道帶著獨到的佛學意趣,發展出了獨到的佛學成就,文學作品流露著淡淡的佛學意韻。
參考文獻:
1.《袁中郎隨筆》劉琦注,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識張幼于箴銘后》
2.《袁中郎隨筆》劉琦注,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敘小修詩》
3.《袁中郎隨筆》劉琦注,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江進之》
4.袁銑《重刻梨云館本敘》
5.《袁中郎隨筆》劉琦注,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敘小修詩》
6.馬杰、陳學通《文教資料》,2006年8月
7.《袁中郎隨筆》劉琦注,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黃平倩》
8.《袁中郎隨筆》劉琦注,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龔惟長先生》
9.《袁中郎隨筆》劉琦注,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徐漢明》
10.周群《袁宏道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第130頁
11.《袁中郎隨筆》劉琦注,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顧升伯修撰》
12.周群《袁宏道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第130頁
13.周群《袁宏道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第134頁
14.戴紅賢《袁宏道與晚明性靈文學思潮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第142頁
作者簡介:
肖雨童,女,2018年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現就職于五臺山風景區管委會
聯系方式:15386800153(微信同號)
郵箱:603468189@qq.com
通訊地址:山西省忻州市五臺山風景區臺懷鎮大顯通寺宗教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