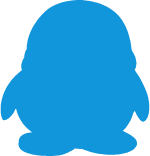竺霞上人
竺樸雄健巴山開, 霞明玉映行無礙。
上窮華嚴下泥潭, 人間游化太虛臺。?
竺老是我受戒時的羯磨阿阇黎,是我在重慶佛學院學習時的院長,是我在四川省佛學院求學時的師長。
竺老誕辰100周年的時候,心里想著要將對老人家的緬懷寫成文字,但那一年病魔、雜務纏身,最終沒能實現這一愿望,十年來內心一直心存愧疚,滿心的歉意。今年是竺老誕辰110周年,以此契機,將多年來對他老人家的敬意和感恩化作文字,用以紀念竺老簡樸而又閃爍著慧光的一生。
竺老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川渝兩地頗有影響力的高僧大德。竺老青年時代曾入雙桂堂佛學院、華嚴佛學院、漢藏教理院學習,是太虛大師的主要弟子之一。
竺老生前曾擔任過四川省佛教協會、重慶市佛教協會領導職務,住錫重慶羅漢寺法席,創辦重慶佛學院,積極推動建寺安僧、開展法務、培育僧才、扶危濟困、對外交流等工作,為川渝兩地劫后佛教事業的恢復做出了重要貢獻。
竺老生前還擔任過重慶市南岸區人大代表、渝中區人大代表,重慶市人大代表,重慶市政協委員,積極協助黨和政府貫徹落實宗教政策,參政議政,建言獻策,熱心公益,關心社會,得到了黨和政府的肯定和認同。
竺老一生保持樸素的生活方式,一生堅持樸實的行事風格,一生奉持質樸的待人之道,一生恒持謙和的處眾風范。正因為竺老身上所具有的樸素、簡樸、質樸、謙和等光輝品格,深受四眾弟子愛戴,也是我景仰和學習的榜樣。
一、投身佛門 奉獻一生
竺老生于1911年,俗姓徐,名裕亮,重慶墊江普順人氏。父徐公書富,母夏氏,行十三,除一兄一姊外,其余皆相繼病夭。
八歲時入徐氏祠堂私塾隨熊老先生學習,先后讀誦《三字經》《千家詩》《論語》《孟子》等儒學經典,閑時閱讀《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傳》等白話小說。
十二歲入普順中心小學,學習《國文》《算學》《歷史》《輿地》《音樂》《圖畫》等科目,大量閱讀《史記》《漢書》《唐詩》《宋詞》《七俠五義》《封神演義》《聊齋志異》《濟公傳》等文學作品。對小說《濟公傳》中塑造的人物濟公十分崇拜和向往。
1928年,竺老在父親的支持下投梁平縣仁賢鄉西禪寺,禮福江上人剃度出家,法名圓相,字斯壽。因崇拜濟公,自號粥俠,又號燭瞎,后取諧音,改名竺霞,后以此號行世。

梁平雙桂堂舊影
1929年秋,竺老于梁平雙桂堂中道和尚受具足戒,羯磨阿阇黎、教授阿阇黎分別是雙桂堂的退隱月朗和尚、圓庸和尚。
離開西禪寺小廟,到大叢林雙桂堂學修,對任何一位初發心的出家人來說,都是一件十分高興的事,竺老的內心也自然充滿了喜悅。這可以從他當時留下的詩文中感受到,詩曰:“稻黃雀飛秋氣清,白云伴我雙桂行。世情不解僧居樂,習禪學凈心自寧。”
戒期結束后,考入設于寺中的雙桂堂佛學院。在雙桂堂佛學院學習期間,葦舟法師講授的《折疑論》、雙桂堂方丈中道法師講授的《法華經》讓他大開眼界,讓他對佛學教理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特別是國文教師唐宏文講授《聲律啟蒙》,讓他的詩文造詣有了很大的進步,唐先生曾以“光明世界”四字為聯出句,竺老以“黑暗叢林”為對,深受唐先生贊許。后唐先生借與竺老傍晚在石桌旁納涼的機會,曾以“二人同坐土上”為聯出句,竺老一時難以為對,直到晚年于夢中對以“一馬獨闖門中”一句,甚為滿意。
在雙桂堂佛學院學習兩年,由于他的勤奮和刻苦,在五十名左右同學中總是名列前茅,并以優異成績畢業。

1981年,中國佛教協會舉辦傳戒活動。圖為傳戒十師留影
1931年,竺老為了繼續深入研習佛法,離開雙桂堂佛學院只身前往重慶,經介紹到設在放牛巷的華嚴佛學院求學。
華嚴佛學院院址是一棟四層樓的青磚洋房,原是金鑫人壽保險公司的辦公用房,后公司難以為繼而解散,公司經理甘海泉居士在此創辦華嚴佛學院,聘請畢業于月霞法師在上海所辦華嚴大學的慧西法師駐院講授《華嚴經》,初期以“研習華嚴”為宗旨。
一年多后,遷南岸大佛寺,后因創辦人改宗旨為“讀誦華嚴”,引發罷課風波,竺老與開一同學在風波中因表現突出而受傷。
風波后,竺老與部分同學隨慧西法師到長安寺繼續研習《華嚴經》,期間蒙巴縣縣長馮均逸先生的幫助,慧西法師率學僧遷住巴縣白市驛鎮曾家場蓮花寺佛學院,竺老得以繼續追隨慧西法師研習華嚴,除了聽慧西法師講授《華嚴經》外,學院還開設有佛教史、各宗大意等課程。
竺老隨著華嚴佛學院遷徙,前后五年時間專心研習華嚴,對華嚴圓融無礙的思想有了深刻的體悟,這為他養成樸實謙和的僧格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37年,竺老已從華嚴佛學院畢業,心里生起赴江南繼續深造的愿望。是年6月,隨慧西法師從朝天門碼頭乘“福緣號”客船出發,前往上海,在客船上結識“福緣號”領江向興發,對向領江的虔誠信仰和平等善行極為推崇。
到上海后,暫住位于四川路的彌陀寺。期間與新結識的年輕僧人戒度法師前往普陀山,朝禮觀音菩薩道場。朝圣結束后,返回上海,仍住彌陀寺。
由于抗日戰爭爆發,隨旅滬同鄉會乘海船抵達廈門,經廈門繞道香港,由香港到達廣州,從廣州乘車到武漢,在劉湘駐武漢辦事處的接濟下,乘船返回重慶。受戰事的影響,近一年的顛沛流離,外出求學的愿望最終沒能實現。

太虛大師創辦的漢藏教理院
1938年,竺老在與華嚴佛學院同學開一法師的通信中,決定前往太虛大師于1932年在北碚縉云山創辦的漢藏教理院繼續深造,考入該院第三期普通科,并擔任班長,得以親近太虛大師、法尊法師、法舫法師等高僧大德,還經常聆聽名人學者的演講。
竺老在學院學習四年,不僅佛學造詣更精深,兼及藏文、政治、哲學、歷史等課程,讓他的見識和胸襟更加的廣博和寬闊,這為他日后成為一代高僧積淀了深厚的學養。
竺老在學院畢業時,以優異的成績和人品獲得太虛大師的贊許,曾親筆書贈“竺國梵僧傳佛法,霞天錦地露心光”聯語,以資印可。

漢藏教理院舊址
1942年,竺老從漢藏教理院畢業后,隨嚴定法師赴榮昌創辦寶城佛學院。1946年應正果法師邀請回漢藏教理院任教,直至解放。1950年至1956年蟄居梁平西禪寺。
1956年應開一法師邀請回縉云山協助政府開展“內查外調”工作。1960年安排在羅漢寺素餐廳售票,后成為前進綜合加工廠的一員,專門糊紙盒、扎掃把。
1967年隨羅漢寺僧人遷住位于通遠門下和平路天寶下院。1970年隨全市佛道教人員集中南岸慈云寺進行勞動改造,后被選為生產主任。1977年當選南岸區人大代表。
1980年,竺老迎來了人生的重大轉折點,是年調任羅漢寺住持,肩負起羅漢寺恢復重建工作,并將自己晚年二十余年的時光,全部奉獻給了羅漢寺。

1987年,竺老與正果長老、惟賢長老在重慶羅漢寺
竺老擔任羅漢寺住持時,羅漢寺的建筑已經朽壞不堪,主要建筑被其他單位占為他用,昔日羅漢堂的羅漢已化為灰燼,面對滿目瘡痍的殘破寺院,內心只能默默地發愿,期待能逐步重建。1983年,羅漢寺被國務院列為全國漢傳佛教重點寺院之一。
在黨和政府的支持下,率先培整修復了大雄寶殿,新塑釋迦摩尼、文殊、普賢三尊圣像,滿足開展基本的佛事活動。同時在竺老的多方奔走呼吁和長期努力下,占用羅漢寺房屋的相關單位直到1985年才陸續遷出。
竺老趁勢而為,積極倡導重建羅漢堂,邀請四川美術學院和重慶建筑工程學院的師生負責塑像工程。在各方的默契配合下,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羅漢堂終于重新建成。
繼后,竺老精心籌劃,相繼主持修建了濟公殿、法堂、藏經樓、禪堂、彌勒閣、妙香齋等殿堂和附屬設施。雖然沒能恢復舊觀,但在現實條件下,已讓羅漢寺成為功能齊備的莊嚴道場,這都凝聚著竺老的汗水、心血和智慧。

重慶羅漢寺新貌
竺老在擔任羅漢寺住持期間,工作重心主要放在羅漢寺的整體恢復和發展,而對于寺院具體日常事務的管理,總是以“無為而治”的工作方式,放手讓各寮口的執事們酌情處事,注重發揮執事們的特長,調動執事們的工作積極性。因此,在寺院里,竺老常常被大家誤以為“柔弱”,實際上這也是一種處事智慧。
1982年當選為重慶市佛教協會副會長,1987年先后當選為重慶市佛教協會會長、四川省佛教協會副會長、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1993年任四川省佛教協會名譽副會長、重慶市佛教協會名譽會長、中國佛教協會咨議委員會委員。1997年重慶直轄后,退羅漢寺院事,讓賢大果法師繼任法席,并任重慶市佛教協會名譽會長。
2003年十二月十八日,竺老于羅漢寺退院寮安詳示寂,世壽九十三歲,僧臘七十六年,戒臘七十五夏。

1985年,竺老在寶光寺傳戒活動上
竺老投身佛門近八十載,在他的僧侶生涯中,有近二十年時光是在佛學院求學、辦學、教書育僧中度過的;有近三十年時光是輾轉各寺院,在社會變革、運動、改造中度過的;有二十余年時光是在羅漢寺的恢復、重建、開展教務、接待應酬中度過的。
竺老的一生,始終堅守自己的信仰,順境時奉獻佛門,逆境時蟄居佛門,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佛教事業,不愧初入佛門的誓言。
二、慕虛大師 育僧育才
太虛大師是二十世紀杰出的高僧,是引領傳統佛教轉型走入現代社會的佛門領袖,在當時全國佛教界享有崇高的聲譽,特別是其遠見卓識和深邃的智慧引領時代先鋒,深受青年僧伽的仰慕和崇敬,竺老便是這眾多青年僧伽中的一員。

漢藏教理院舊址
1930年太虛大師到四川弘法,在四川省主席劉湘的支持下,擬創辦漢藏教理院,聯絡漢藏感情,溝通漢藏文化。
經四川省建設廳廳長兼重慶警察局局長何北衡先生具體操辦,選定北碚縉云寺作為院址,經過兩年的籌備,于1932年秋正式開學,劉湘任名譽院長,太虛大師任院長。
學院以“淡寧明敏”為院訓,設普通、專修兩科,普通科學制四年,專修科學制兩年。普通科分甲乙兩班,乙班兩年畢業轉為甲班,甲班兩年畢業后可升入專修班。
學院在太虛大師的指導下,高僧大德云集,名師薈萃,師資陣容雄厚,一時成為青年僧伽向往的佛教界最高學府。特別是抗戰爆發國民政府遷重慶后,太虛大師常駐學院講學,漢藏教理院更引起青年僧伽的關注。
正是在這一時期,竺老于1938年考入漢藏教理院,得以朝夕親近太虛大師。學習期間,有名師教導,有名家引領,有名賢交往,學修都獲得了巨大的進步。當時漢院的學僧不僅能親近高僧大德受教,還有許多政要和社會名流慕名到學院參觀或演講。
竺老在漢院求學時,先后聆聽過郭沫若、林語堂、梁實秋、老舍、翦伯贊、馬寅初、馮玉祥等名家名流的演講,令他眼界大開。
在四年學習中,深受太虛大師思想影響,并折服于太虛大師為法為教的熱忱和擔當,成為太虛大師賞識的弟子之一,并立志追隨太虛大師,終其一生繼承太虛大師育僧育才的志業。

榮昌縣寶城佛學院舊址
竺老在漢院學習期間,還與謝無量夫婦、馮玉祥將軍成為忘年之交。在漢院學習的第三年,受法尊法師指定,竺老負責指導謝無量先生的夫人學習藏文。在一次指導學習中,謝夫人看見亭旁的荷花,隨口吟出了譚嗣同題憩園的上聯“人境影中,被一片花光團住”,竺老即刻對出“霜華秋后,看四山嵐翠飛來”下聯,深得謝夫人贊賞。后在與謝無量先生佛學經義的切磋中,成為忘年交,謝無量先生還專門送給竺老一副書法作品,以為紀念。
竺老學習期間,與來山小住的馮玉祥將軍甚是投緣,馮先生離開縉云山時,還特別以隸書寫下一副以“天下為公”為內容的書法作品相送,可見馮先生對竺老的敬重。
1942年,竺老從漢藏教理院畢業,由于已經有了十余年的佛學院研修生涯,已然成為一名德才兼備精通佛學的法師。畢業后,受老師嚴定法師邀請,到榮昌興辦佛學院。
嚴定法師,籍貫湖南,早年畢業于武昌佛學院,后赴西藏學習,是太虛大師弟子中佼佼者,曾在四川大學任教,頗受師生歡迎和敬重。應榮昌參議長陳漢傳先生及夫人趙懋云女士(榮昌女中校長)的邀請,赴榮昌縣城西門外寶城寺創辦寶城佛學院。
嚴定法師赴任時,挑選了漢藏教理院的學生竺霞、演清、悟嚴諸師一同前往,協助教務,襄助院務。到院后,竺老被任命為教務長,在嚴定法師的指導下,負責教學安排,設置課程,編定課表,有時還要親自印制教材。竺老除了承擔教務事務工作,還要全身心投入教學中,先后為學生講授了《五蘊論》《百法明門論》《俱舍論》《古文觀止》等課程。

榮昌縣寶城寺內的太虛經樓
由于竺老在寶城佛學院辦學認真負責,頗具影響,還被推選為榮昌佛教會理事長。最令竺老深受鼓舞的是,1943年1月,自己最尊敬愛戴的太虛大師來到榮昌,親眼看到自己的學生能將佛學院辦得頗有成效,領會自己培養人才的苦心,太虛大師非常贊賞,并親自書寫一聯“棠宴蓮開,三千世界嚴香國;玉瓶桃熟,五百由旬達寶城”贈與寶城寺及佛學院,這既是對自己學生的認可,更是對得意門生的鼓勵。竺老深受感動,內心感到無比的榮光,也更加堅定了自己為佛教培養僧才的信念。
1946年春,由于抗戰勝利后漢藏教理院許多教員都回了江南,太虛大師也離院到了上海,正式任命法尊法師擔任院長。此時學院師資隊伍出現短缺,擔任教務長的正果法師,報請院長法尊法師同意,聘請竺老回漢藏教理院擔任訓育主任兼佛學教授。
竺老從漢藏教理院畢業已經四年了,重上縉云山,睹物思人,無限感慨。作為訓育主任的竺老,肩負起全院學生的品行修持督導,還要率先垂范,為學生日常生活和學習操勞。竺老還為學院第五期學員講授《俱舍論》和《比丘學處》等課程。
竺老在課堂教學和學生管理工作中,始終貫徹太虛大師“人成即佛成”的佛學思想,堅持佛教精神與現實人生圓融匯通的原則,注重學生的基本品德和修養,善于耐心和學生溝通,心平氣和與學生交流談心,成為法尊法師和正果法師的得力助手。
1947年3月17日,一代佛門領袖太虛大師在上海玉佛寺辭世,慧星隕落,法門折幢,佛教界失去了一位先鋒巨匠,漢藏教理院也失去了靈魂導師,讓全院師生陷入了無盡的悲痛。
院長法尊法師當即赴上海奔喪,竺老協助正果法師料理院務,并組織追悼活動。從當時學院里的兩幅挽聯中,可以感受到漢院全體師生對太虛大師的愛戴、崇敬、不舍、惋惜。一聯曰“四十載拯救培僧,悲志未酬,何堪遽返兜率;五大洲宏宗濟世,慈心無已,惟望再來閻浮。”另一聯曰“為國宣勞,為教宣勞,際茲大亂未平,方冀長資慧日;舍僧而去,舍世而去,悲夫復興甫望,何堪遽殞良師。”

重慶漢藏教理院太虛大師之塔
追思太虛大師的同時,全國各地的師生和追悼委員會決定為大師出紀念集,向各位師友發出了征稿倡議,五十余位師友都撰寫了紀念文章。紀念文章匯集后,由漢藏教理院同學會編輯為《太虛大師紀念集》,在漢口三民印書館出版發行。
紀念集收錄了竺老當時撰寫的紀念文章《太虛大師判攝一切佛法之研究》,文章是從繼承太虛大師佛學思想的角度展開的,重點闡述虛大師所倡宏的“今菩薩行”,號召繼承虛大師提倡的“人生佛教”思想。從竺老的文章中,可以感知得到他對虛大師佛學思想精髓的準確把握,不愧為虛大師賞識的學生。
1949年底,新中國成立前夕,戰事消息也頻頻傳到漢藏教理院,學院的學生漸漸人心渙散。期間有不少師友動議,將漢藏教理院遷往海外,院長法尊法師正在成都講學,院務交由正果法師代管。正果法師審時度勢,決定漢藏教理院不隨“國民政府”遷臺,依然選擇留在內地,迎接新的時節因緣。
竺老與正果法師是相知相契的道友,他深知正果法師決定學院不遷海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也佩服正果法師的堅定精神,毅然支持正果法師的決定,與學院師生共同迎接解放。從在漢藏教理院學習,到再回漢藏教理院任教,竺老與正果法師交往最深,從學友到同事,成為了一生的摯友。

竺老與正果長老合影
改革開放后,佛教事業的發展迎來了新的春天,隨著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實,寺院的法務活動也得到逐步恢復,進入佛門的青年僧伽也不斷增多,為了提高青年僧伽的佛學素養和文化水平,竺老的內心又萌生了創辦佛學院的念頭。
1990年,在有關方面的支持下,竺老在重慶羅漢寺創辦重慶佛學院,學院秉持太虛大師的佛學理念和辦學宗旨,招收四眾弟子進入學院學習,學院既有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還有優婆塞、優婆夷。
竺老親任院長,惟賢法師任副院長,陳文杰(漢藏教理院第一期學生,法名同杰)任教務主任。竺老還親自授課,講授《藥師經》,惟賢法師講授《遺教三經》,陳文杰老師講授《佛學概論》,彭宗民老師(1962年畢業于中國佛學院研究部,法名徹洪)講授《印度佛教史》,樊吉文老師(漢藏教理院學生,法名寂文)講授《五蘊論》,甘文峰老師(漢藏教理院學生,曾赴西藏學習,法名寂禪)講授《古典文學》,楊自合老師(1958年畢業于中國佛學院,法名廣平)講授《因明概論》,楊春巍教授(建筑研究院)講授《佛教與科學》。
學院聘請的師資,大部分都是畢業于漢藏教理院,也是太虛大師的學生,大家受竺老的感召,云集于羅漢寺,發揮余熱,盡心盡力,共同繼承太虛大師培育僧才的遺志。

1985年,竺老在成都寶光寺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隆蓮法師在有關方面的支持下,在成都鐵像寺創辦了具有全國性佛教院校的四川尼眾佛學院。
創辦之初,由于師資匱乏,竺老還應隆蓮法師之邀,專程到學院為青年尼僧講授《大乘五蘊論》等課程,以實際行動表達對隆蓮法師的重視尼僧教育和人才培養的支持。從某種意義上講,竺老的這一看似平凡的舉動,不難看出受太虛大師思想影響的影子。

1987年,參加第五屆佛代會的原漢藏教理院師友合影
竺老一生仰慕并追隨太虛大師,一生對太虛大師的敬重之情不減。太虛大師五十壽辰時,漢藏教理院師生曾在獅子峰筑有“太虛臺”以為紀念;太虛大師圓寂時,漢藏教理院師生曾在縉云寺旁建有太虛大師舍利塔。“文革”中,“太虛臺”和太虛大師舍利塔皆被毀壞。1988年,為緬懷太虛大師的豐功偉績,竺老發起在原址重建了“太虛臺”和太虛大師紀念塔,并請虞愚先生重寫了“太虛臺”并刻石,請趙樸老題寫了“太虛大師之塔”,竺老親自撰寫了“智通三藏,機應五乘,曠代高僧傳千古”上聯,洪禪法師撰寫了“學貫古今,名揚中外,四洲弘法第一人”的下聯,篆刻于塔的兩側,表達了兩代學生對太虛大師的緬懷和贊頌之情。

1985年,竺老在寶光寺傳戒活動上
竺老與漢藏教理院學長正果法師成為摯友,對正果法師的尊重之誼不退。“文革”結束后,宗教政策逐步落實,1979年5月,竺老北上,到北京廣濟寺探望師長法尊法師、學長正果法師。竺老在廣濟寺住了一個多月,三位師友分隔二十余年后重逢,內心無比感慨,三位老人余生劫后再敘,相聚甚歡,徹夜長談,談他們的老師太虛大師,互相交換昔日師友分散后的信息和情況。正果法師還特別派人陪同竺老,到北京各寺廟及名勝古跡游覽,竺老也已近古稀之年登上了萬里長城,站在長城頂上,內心無比期待佛教的復興能夠逐步走上軌道。
1987年1月,正果法師回到闊別了三十七年的重慶,竺老陪正果法師一起到慈云寺、雙桂堂等處參訪,還特別陪他上縉云山,探訪漢藏教理院舊址,故地重游,了卻夙愿。正果法師回京后,就在這一年的11月20日在廣濟寺圓寂,重慶之行,成為了正果法師于竺老生前的最后一次面敘。
正果法師圓寂后,竺老為表達對這位學長的敬重,提議將正果法師的靈骨塔建在縉云山,得到了趙樸老和中國佛教協會的支持,委托竺老親自承辦。1990年11月21日,正果法師靈塔在縉云山太虛大師塔旁落成,趙樸老題寫了“正果法師之塔”,塔側刻有鄧穎超題寫的挽聯“論其生平,以發揚佛教優良傳統為職志;廣為信眾,樹熱愛社會主義祖國之楷模”。在竺老的努力下,正果法師又回到了他學習和工作過的熱土。

圖為竺霞法師靈塔(左)、正果法師靈塔(右)
2003年冬,竺老圓寂荼毗后,在重慶市佛教協會的支持下,決定將竺老的靈塔也建在縉云山,與太虛大師、正果法師靈塔毗鄰。
三位師友相敬、相知,長臥于昔日生活學習工作的地方,也可謂是一段殊勝的因緣和佳話。
三、終身淡泊 高風共仰
竺老不僅全身心投入羅漢寺的恢復重建和弘法事業,他還積極主動地關注重慶、四川乃至全國佛教界的教務工作,推動和支持各地落實宗教政策,恢復佛教活動場所。
他還特別關心青年僧伽的接引工作,多次參加傳戒活動,擔任重要師承,為培育后學不辭辛勞。

1981年元旦中國佛學院學僧受具足戒,圖為戒子與十師合影
1980年底,中國佛教協會第四屆全國代表會在北京舉行,這是“文革”結束后全國佛教界第一次盛會,備受矚目。
在這次會議結束后,經趙樸老提議,由正果法師具體操持,在中國佛教協會駐地廣濟寺舉行了中斷二十余年的傳戒活動,為剛入學的中國佛學院學生傳授三壇大戒,也有部分在“文革”中受形勢所迫還俗又重新回到僧團的僧人一并重新受戒。竺老被禮請為此次傳戒活動的十位戒師之一,擔任第六位尊證阿阇黎。
此次傳戒是“文革”后第一次傳戒活動,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是經歷劫難后中國佛教界僧團重新吸收新生力量的標志性事件,竺老不僅見證了這一特殊歷史,還成為了這一歷史的參與者,這不能不說是他人生中值得記錄的殊勝經歷。

1985年,竺老在寶光寺傳戒活動上
1985年秋,“文革”結束后四川省佛教界第一次傳戒在新都寶光寺舉行。由于這是全川中斷三十余年首次舉行的傳戒活動,叢林制度難以為繼,勘為戒師的尊宿也十分匱乏,為了如法如律辦好此次傳戒活動,在四川省佛教協會的主持下,從全川名山大寺遴選德高望重的戒師,成都文殊住持寬霖老和尚被禮請為得戒和尚,樂山烏尤寺住持遍能老和尚被禮請為羯磨阿阇黎,竺老被禮請為教授阿阇黎,成為此次傳戒活動的三師之一,實在是非常殊勝的因緣。
正是這次傳戒活動的舉辦,為四川佛教界接引了一批新生力量,為緩解青黃不接的窘迫,起到了重要作用,竺老功不可沒也。

1985年,寶光寺傳戒盛況
此后,竺老于1987年秋新都寶光寺傳戒活動被禮請為羯磨阿阇黎,1987年冬云南雞足山祝圣寺傳戒活動被禮請為羯磨阿阇黎,1990年秋新都寶光寺傳戒活動被禮請為教授阿阇黎,1991年冬成都昭覺寺傳戒活動被禮請為羯磨阿阇黎,1993年夏洛陽白馬寺傳戒活動被禮請為第一尊證阿阇黎。

1987年秋新都寶光寺傳戒活動
竺老以古稀之年投入佛教劫后復興事業,既是地處繁華鬧市區重點寺院的住持,也是省市佛教協會的負責人,還肩負有參政議政的社會職務,可謂身居要職的川渝佛門領袖。
作為寺院的住持,他有證授皈依的眾多在家弟子,作為參與傳戒活動的佛門大德,他有數千計的出家弟子,在川渝僧俗弟子中有巨大的影響力。盡管如此,他始終保持僧人本分、衲子本色,視名利如浮云,泰然處之,常年以謙和、低調、樸實的面貌應世接物。
他總是深居簡出,不搞個人享受。記得1992年初,我到重慶佛學院求學,剛到院安頓好后,去向他禮座。竺老是我受戒時的三師之一,以羯磨阿阇黎的身份成就我的戒品,按佛門傳統禮儀,我理應去向他禮拜供養。
我搭衣持具去輕叩他的住所,當時羅漢寺的藏經樓竣工不久,設在藏經樓一層的丈室還沒有完全整理好,他住在大雄寶殿西邊一幢四層樓的磚混建筑里,那幢樓是當時的招飛辦遷出后留下的,他的寮房在第二層最邊上的一間。
我先是向他呈白求學的意愿后,展具向他頂禮,他慈悲地堅持讓我不用展具、不用頂禮,并簡單地詢問了我出家的一些情況。當得知我是從昭覺寺來,是昭覺寺原監院智益上人的弟子,囑咐我要好好學習,好好發心,以師父為榜樣。
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這么有影響力的一位大德,寮房里就一張簡易的木床,一個木制書柜,一張書桌,一張藤椅,一個木制洗臉架,暖壺、面盆和日常生活用品外,別無他物。
我入學后不久,他遷入了新的丈室,記得還去向他請教過兩次問題,丈室里的陳設依然是那樣的簡單,除了樸實以外,沒有任何的華麗陳設。竺老的生活作風,當時就給我的內心極大的觸動,至今回憶起來,仍然心存敬仰。

1987年冬云南雞足山祝圣寺傳戒活動
他衣著格外樸素,生活極其簡單。他的著裝都是以粗布簡料為主,從不追求光鮮麗質,有的衣裝甚至是從“文革”中的衣服加以改制而成,所以大家常常會見到他穿的短褂有時會有四個衣兜,甚至上面兩個衣兜會有翻蓋,很明顯這樣的衣服是從中山裝改制過來的,只是將原來的領子改作了大領,一方面是當時經濟條件有限,另一方面也是中華文化惜福惜物傳統的體現,這樣的改制僧服,他一直舍不得廢棄。
他重新復出的時候,已經是古稀之年的老人,本可安度晚年,但他以瘦弱之軀肩負起了歷史的重任。他外出時,幾乎不帶隨從,為了行動安全起見,所以他穿的中褂、大褂下擺都比較短,就是為了出門方便。
正是由于他的著裝并不講究,因此有的人對此頗有微詞,但他從不解釋,依然樸素簡潔,但求心安。他一日三餐幾乎是隨大寮餐食,從不講特殊。
由于羅漢寺空間狹小,建筑擁擠,在我求學的時候,還沒一個像樣的齋堂供僧眾過堂用齋,當時常住僧眾和學僧都是桌餐,他有時也會與同學們一道用餐,有時候會讓侍者從大寮取餐回寮房用餐,絕不講個人享受。

1990年秋新都寶光寺傳戒活動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羅漢寺的恢復重建已初具規模。竺老年事漸高,常常有精力不濟之感,于是著手思考羅漢寺未來的發展。經多方考慮,并得到有關方面的支持,他決定推舉大足寶頂山圣壽寺住持大果法師繼任羅漢寺法席。
1996年冬,敦請大果法師任羅漢寺首座,請他入住羅漢寺,熟悉羅漢寺內外寺務,逐漸醞釀新老交替工作。
1997年因緣逐漸成熟,是年深秋,竺老完成了他住持羅漢寺繼往開來的一件大事,將羅漢寺法席傳付大果法師。傳法偈一曰:獨登絕頂尋攀緣,放眼觀察遍大千;人法性空緣起有,西來真諦而今傳。此偈可以窺知到他一生在佛法學修中的領悟。傳法偈二曰:如來家業擔非輕,護國安僧一肩承;慧命傳燈無盡藏,人天處處法王城。此偈即是他對新任住持的厚望,也對羅漢寺的未來充滿了期待。
佛門中常有“提起容易放下難”的諺語,竺老以他對佛陀教法的深刻體悟和智慧,以他對佛教傳燈事業的高度責任感和使命感,不戀權位,不為名利所困,他不僅如此說,還如是行,該提起的時候義無反顧,該放下的時候云淡風輕。竺老身上這種淡泊名利,主動讓賢的亮節高風,值得后輩學習和發揚。

竺老與惟老于峨眉山萬年寺
竺老卸任住持后,搬入了退院寮,雖然卸去了繁重的寺務,但他的生活依然閑適而有規律,每天清晨依然堅持他練習了幾十年的“達摩十二手”,白天則堅持讀經、看報,常常也會關心時事,遇有弟子或信眾來拜望,他都會慈悲接應,簡單開示,鼓勵他們精進學修。
由于他的廣泛影響力,九十大壽時,他順應弟子們的愿望,過了一次生日慶賀,弟子們為他操辦的很是熱鬧,但他內心仍和往常一樣淡然,并在自己的九旬留影上題了一首詩:“日落西山憶故鄉,即須檢點辦資糧;等閑整頓好行李,莫到臨時手腳忙。”他通過這首詩,表達了自己的生死觀,這種對生死的超然和曠達,是他幾十年在佛法修為境界上的流露。
正如他自己所愿,以九十三歲高齡辭世的時候,當天堅持從醫院回羅漢寺,回到寺院退院寮后十余分鐘,便安詳圓寂,真正做到了“等閑整頓好行李”的功夫,展現出“莫到臨時手腳忙”的禪者風范。
四、法乳一滴 恩深似海
我初出家的時候,完全是出于信仰的情感,對佛法教理是茫然無知的空白狀態,如果說今天對佛教教義有一點認知的話,那第一站便是在重慶佛學院學習時奠定的基礎。

1990年,竺老與遍老、清定上師
1992年春,我在重慶佛學院學習時,竺老為我們講授《藥師經》。記得前面兩堂課并沒有直接涉及到《藥師經》的內容,而是為我們講述他為什么重視弘揚《藥師經》的思考,從玉琳國師修持《藥師經》的感應,講到弘一大師弘揚《藥師經》的典故。
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講解中指出,佛教界對大雄寶殿中供奉三尊佛像的認知存在差異,有主張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佛的,有主張法、報、化三身佛的,他從教理上分析后都不贊成。
他說:過去佛誰見過,現在佛誰遇見過,未來佛來都還沒有來,怎么可能用具像來表達。他還說:法身佛盡虛空遍法界都是,并無形象;報身佛是地上菩薩才可以見,凡夫是不能以肉眼見的;至于化身佛,也是化現不同身份度化眾生,哪有固定的形象。因此,他極力主張大雄寶殿中供奉的三尊佛像,應當中間為釋迦牟尼佛,左邊為藥師佛,右邊為阿彌陀佛。
他還從教理上為我們分析,釋迦牟尼佛應化娑婆世界度化眾生,就是要解決現實的“生”和“死”這一根本問題,左邊的藥師佛就是協助釋迦牟尼佛解決眾生“生”的問題,右邊的阿彌陀佛就是協助釋迦牟尼佛解決“死”的問題。
他自己之所以重視弘揚《藥師經》,就是要倡導學佛的弟子要更加重視“生”的問題,因為阿彌陀佛的凈土法門比較流行和普遍,比較能解決學佛弟子生命結束(“死”)的問題,但不能一邊倒,不然有失偏頗,不利于佛陀教法的全面弘揚。
他在講解中說,不解決好“生”的問題,“死”的問題也不一定會圓滿,解決好了“生”問題,“死”的問題也自然會迎刃而解,弘揚《藥師經》,就是要大力弘揚藥師法門,倡導佛弟子以藥師佛的十二行愿,積極過好現實的人生和生活。今天看來,竺老的這些見地和主張,是與太虛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一脈相承的。

重慶羅漢寺羅漢堂
1993年秋,我在四川省佛學院學習,時任院長遍能法師先后邀請各地諸山長老來院講學,竺老在這期間應邀為我們高級班學員講授《八識規矩頌》。
竺老來院時,已是八十二歲高齡,沒有攜帶侍者,我時任班長,受學院委派負責照顧他的生活起居,但他并沒有給我增添麻煩。
一天清晨,可能由于他不太熟悉環境,晨練時摔了一跤,手掌及膝蓋皆都磕的紫青,可把我給嚇壞了,好在他的身體還健朗,并沒有什么大礙,只是吩咐我去醫務室拿了幾貼膏藥敷上,仍然為我們繼續上課。
竺老講解《八識規矩頌》時,參考教材是范古農居士的《八識規矩頌貫珠解》,他自己也不帶書,就是空手走上講臺,一支粉筆放在講桌上,坐在講臺上侃侃而談,偶爾會起身用粉筆寫上生僻的佛學名詞。
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講解與眾不同,他講解頌文的順序,是按照染、凈分類的原則逐句講解,先將每一類識的染污兩頌按第六識、前五識、第八識、第七識的順序講解,后將每一類識的凈分一頌按第六識、第七識、第八識、前五識的順序講解,這種與眾不同的講授方法,對我們新學習的學生來講,可謂別開生面,面貌一新。他最后才告訴我們,這是太虛大師的講授方法,在他的引導下,同學們對太虛大師也生起了格外的敬仰。
后來,竺老還在羅漢寺以同樣的方法講解過《八識規矩頌》,蔡榮賢居士非常用心,將講解全部記錄成文字,后編印成《八識規矩頌淺釋》印行。
1995年春,我與幾名在中國佛學院學習的同學到重慶參學,在羅漢寺掛單。初到羅漢寺時,我照例去向他禮座,奉上300元的供養金,當時老人家滿心歡喜地接受了供養。
哪知到了第二天,我正在羅漢寺一名執事的辦公室與各位同參敘舊,時任羅漢寺監院的智凱法師(1949年前曾在漢藏教理院務工,并親近正果法師;改革開放后依竺老剃度出家)來到辦公室,遞給我一個紅包,說是竺老讓他轉送給我的,并讓智凱法師轉達說,我是讀書的學僧,單金是很有限的,他哪里能收窮學生的供養。我也是不懂規矩,當著大家的面拆開了紅包,發現不僅原來供養的300元人民幣在其中,而且還多了三張100元的美金。
我當時一下驚呆了,站在原地沉默了好一會兒,霎時間我才明白,竺老送回來的不只是一個紅包,而是滿心的鼓勵和厚愛,當即我請智凱法師轉達了對老人家的感謝。
這看起來是一件不起眼的事,但竺老對待供養的隨緣淡泊,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讓我深受教育,心中對他的崇敬也油然而生。這件事雖然過去二十多年了,但它一直留在我記憶的深處,因為我體會到,老人家送回來的不僅僅是錢,而是他對后輩學僧的關愛,這是一份沉甸甸的慈悲之情,這份愛護之情,我一直珍藏至今,偶爾回憶起來,內心仍然充滿了溫暖。

2003年,竺老在文殊院升座活動上
竺老對我而言,不僅有佛法的啟蒙之恩,他還在我日后的成長過程中,給予了極大的提攜和幫助。2001年秋,我已從中國佛學院畢業到文殊院常住,時任文殊院監院的廣福師與常住諸師商議,準備舉辦為時一個月的“講經弘法月”,邀請川渝兩地高僧大德蒞臨文殊院空林講堂宣說法音。
講經舉辦前,文殊院寂真法師受派遣前往重慶,邀請竺老和惟老一同前來相助盛舉,也正是在這次講經活動,我為大眾講授了十七天的《金剛經》,為成都佛教界所熟知。講經開始的第一天,舉行了迎請和開座儀式,竺老、惟老真是慈悲高風,攜我一同受請和登座,正式開啟了為期一月的講經活動。
后來我才得知,在傳統叢林中,青年法師登座講經時,都有自己的師長護持引領登座,代表前輩對后輩的印可,名為“開大座”。竺老、惟老是德高望重的前輩,我自己并沒有這樣大的福報,能獲得如此殊榮,完全是二老的愛護和栽培,提攜之恩永生難忘。

2003年,竺老在文殊院升座活動上
2003年秋,我繼任文殊院住持,舉行升座儀式,由于是年有“非典”疫情,升座儀式的規模不宜過大,但我還是懷著崇敬的心情給竺老奉送了請柬。
令我感動的是,已很少外出的他,居然破例舟車勞頓前來參加活動,并至始至終見證了升座儀式的全過程,還參加了升座慶典,這份對后輩莫大的支持和關愛,對我的成長是殊勝的醍醐加持。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竺老參加完這次活動回到重慶三個月,就舍報西歸了。噩耗傳來時,內心無比悲痛,當時我受命正在籌備恢復成都大慈寺開放事宜,沒能及時趕去為竺老助念。
在竺老出殯荼毗的前一天夜里,我匆匆趕赴重慶,去送他老人家最后一程。當我趕到羅漢寺靈堂,瞻仰法相,向法體頂禮,凝望靈堂兩側懸掛惟老所撰的挽聯“精研教義,智慧如海,一生辛勞,人天供養,法音響徹千山萬水;住持正法,德行若山,倏爾示寂,眾生同悲,噩耗哀慟四海九州”,頓時眼淚盈眶,無限悲傷。
第二天早上,重慶市佛教界在靈堂為竺老舉行了追思會,重慶市委統戰部、市民宗委領導及有關部門負責人,各地諸山大德,重慶市佛教協會全體同仁參加了追思活動,惟賢法師在追思會上致悼詞,對竺老一生的功德給予了全面的總結和高度的評價。
追思活動結束后,惟老命我為老人家起龕,我強忍悲痛,跪說送行語,將老人家送上靈車,并護送靈龕至梁平雙桂堂荼毗。
在荼毗現場,我突然意識到,竺老十八歲在雙桂堂受戒,以九十三歲高齡走完人生最后旅程時,又回到了雙桂堂荼毗,受戒是正是進入佛門的始點,荼毗是此生落幕的終點,一始一終,同一地點,有始有終,一轉輪回,善始善終,可謂圓滿。
五、結語
竺老的一生,看似平淡,但他一生卻不平凡。他沒有豪言壯語,但他潤物無聲,為佛教事業履職盡力;他沒有驚天動地,但他默默耕耘,為三寶道場傾情奉獻;他沒有掀浪弄潮,但他潛心篤行,為培養僧材矢志不渝。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竺老幼年時,常常體弱多病,身體并不算好,但他能以九十三歲高齡辭世,也算是意想不到的奇跡。
古語有云:仁者壽。竺老的高壽,與他常懷慈悲之心的胸襟是分不開的,也與他一生樸素的生活方式、樸實的行事風格、質樸的待人之道、謙和的處眾風范有著極大的關系。
竺老辭世時,我曾以“門庭有托赴蓮邦,手腳不亂返故鄉。常念法乳失依止,空林月祭嘉陵江”的挽詩,表達對他老人家的深深崇敬之情。
如今,十八年過去了,我對老人家的緬懷和感恩之情,越來越與日俱增。(文/化空 圖/大勢營造古建筑 成都寶光寺)




 我要投稿
我要投稿 返回大菩文化首頁
返回大菩文化首頁 返回資訊頻道
返回資訊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