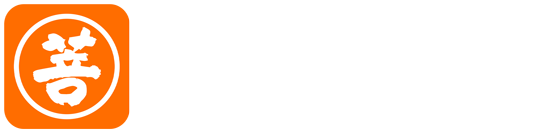玄奘法師是中國歷史上獨步千古的佛門大師,也是古都西安最具標識性的文化名人之一。其西行取經,歷盡磨難,體現了中國人學習域外文化的堅韌精神。




15日上午,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北京大學南亞學系教授湛如法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學“南雍學者”特任講座教授、南京大學東方哲學與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哲學學院教授洪修平,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黑龍江省佛教協會會長、哈爾濱極樂寺方丈靜波法師,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南昌佑民寺方丈純一法師,法鼓文理學院榮休、臺北藝術大學名譽教授、中華電子佛典協會主任委員惠敏法師,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徐文明六位學者大德作主旨發言,為本次研討會奠定研討基調。


印度大乘佛教興起時期,以“大乘”為號等身份性用語隨之盛行。作為中外文明交流儀型,玄奘被印度信奉大乘等人們稱為“大乘天”,其歸國以后,門下弟子們又多有以“大乘”為號者。
從玄奘弟子大乘基、大乘光、大乘恂等“大乘”稱號切入,連接莫高窟“大乘賢者”稱號背后,名號制度與“中國”佛教中心的形成,探討絲綢之路上大乘稱號的周流和歷史意義,可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一、唐代佛教名號制度起源于印度,改造于中土,經唐代國家推動,從佛教僧團習慣性文化發展為國家律令的制度性文化,并周流于亞洲廣大區域;
二、玄奘法師在印度所獲得的“大乘天”稱號,回到中土后由宗教意義逐漸演化出政治意義。傳世文獻所見大乘稱號都是玄奘法師及其弟子,可見師門傳承之意;
三、中國佛教名號制度既包括僧人名號,也涵納寺院名號。這是中國禮樂文明與印度大乘佛教相互融合的一種創造,是中國禮樂文明對印度佛教文明的受容和規范;
四、中土佛教名號文化的歷史影響,為我國歷代政權所繼承發展,甚至被移植至日本;
五、佛教是西域治理的重要方式,既作為當地社會文化、經濟中心之意,更為當地軍隊提供信仰與心靈的關鍵庇護。


洪修平教授從玄奘法師西行求法、譯經、創宗三個層面,概括其對佛教中國化、中華文化繁榮及中印、東亞乃至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貢獻,綜合回顧玄奘法師不同人生階段,對于佛法、制度、文化、文明交流等方面的當世及后世影響:
一、玄奘法師在精通中觀學派和瑜伽行派兩大宗思想基礎上,用梵文寫《會宗論》三千頌,和會空、有兩宗的思想,反對空、有思想割裂。這體現了他對佛學的領會貫通,具有中華文化的圓融思維;
二、玄奘法師譯經基本反映5世紀印度佛學全貌,為中國化佛教宗派創立和佛教中國化理論創新提供理論依據和人才儲備。特別是佛教唯識哲學和因明學的系統傳入,為中國傳統文化添加新內容,也推動隋唐佛教文化的繁榮和思想文化領域三教鼎力新局面的出現,促進中國古代哲學與邏輯學發展;
三、玄奘法師譯經同時又事講學,其弟子中外僧人數千名,為法相唯識宗向外傳播和東亞文明交流互鑒培育土壤。弟子神昉、嘉尚、普光、窺基被稱為“玄門四神足”,開法相唯識宗。隋唐佛教其他宗派創宗人也受玄奘法師及其宗派影響。中外僧人在長安共譯佛殿,從側面映現出中外文化的合作與交流。


靜波法師以《取經詩》開場,強調應重視以玄奘法師為代表的歷代法師堅強、堅毅精神。正是舍身忘死之信念、離苦得樂之慈悲、圓融無礙之智慧與本土文化融合,共同鑄就中華文化的磅礴和自信。
法師表示,玄奘法師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他在譯經過程中保留印度佛教核心思想,同時融入中國特色,嚴謹治學,激勵著后人追求真理。如今大眾對玄奘法師形象或有所曲解,過于片面。佛教應與時俱進,契合時宜,身行言教化解偏見,做好玄奘精神的當代實踐,強化師資,優化資源,培育優秀人才。與此同時,在遵守規范、做好自修的前提下,促進社會和諧穩定,解決當代問題,發揮佛教積極作用。


純一法師選取八世紀中葉時間節點,探討西明寺高僧圓暉和縣曠分別撰述《楞伽經疏》和《大乘起信論廣釋》等文章,在繼承“新譯唯識”思想基礎上,力圖吸收《楞伽經》和《大乘起信論》等“舊譯唯識”的思想現象,并對兩者之間的關系做出新詮釋,提出:
一、圓暉和縣曠的唯識思想反映了中國法相唯識宗從“舊譯唯識”走向新舊唯識兼容的思想轉向。與早期“新譯唯識”信奉者對“舊譯唯識”持排斥、批評立場不同,圓暉主張兩者可以并行不悖。而縣曠則將“舊譯唯識”視為“法性圓融宗”,力圖以如來藏思想融攝唯識思想。
二、隨著法相宗一代窺基、二代慧沼去世,伴隨著武則天政治傾向的支持,“舊譯唯識”呈現出重新奪回話語權的趨勢,《楞伽經》《大乘起信論》等重新受到佛教界重視。法相宗內部對于“舊譯唯識”態度發生變化。
三、“新譯唯識”流行近百年之后,中國佛教界在對“舊譯唯識”和“新譯唯識”之間的差異有了清晰認知基礎上,開始思考兩者之間是否能夠兼容乃至融合。將兩個宗派在思想上連接在一起的就是《楞伽經疏》。這種思想動向發展為建立在“一心”基礎之上的“性相一致”的思想,并成為唐五代之后中國佛教義學的主流思潮。
四、法相宗衰落后,唯識思想主要被華嚴宗所吸收,其如來藏緣起說與“舊譯唯識”深度關聯。


惠敏法師從文獻學角度,探討玄奘法師譯《菩薩戒羯磨文》與慧沼〈大唐三藏法師傳西域正法藏受菩薩戒法〉兩種“授瑜伽菩薩戒羯磨”文獻之異同,并比較二者與《傳戒正范》的授戒科判,以“三段十二門”考察漢傳佛教傳授菩薩戒儀軌演變。
他提出,〈慧沼·別傳本〉可擔任漢傳佛教“授菩薩戒羯磨”的“瑜伽梵網兼容”中介角色,方便訂定“瑜伽菩薩戒法”儀軌,值得當代佛教重視。并就儀軌細節考究、受戒人群適用等提出11項論點。


徐文明教授以北周至隋朝佛教領袖曇延的涅槃學為核心,分析涅槃學及曇延門下弟子對玄奘法師的影響。列舉涅槃學曇延系自曇延法師至法常法師法脈,揭示法常法師為曇延晚期弟子,作為唐初佛教領袖,是玄奘法師貞觀之初的師傅之一。
而曇延最晚門人道洪法師先后參與玄奘法師弘福寺、慈恩寺譯經活動,是唐代涅槃學權威,也是玄奘法師譯經的重要顧問。進一步認識曇延系,對深入了解玄奘法師學術思想有重要意義。



北京大學青藏高原研究院教授、西藏大學文學院副主任薩爾吉作一組總結。從文明交流、沖突、對話角度,使用佛學、文獻學、歷史學、哲學、現代區域與國別研究等學科研究方法,以宏觀視角討論玄奘法式西行求法及佛教中國化歷程。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何孝榮作二組總結。由“玄奘精神當代啟示與詮釋”“玄奘與佛教中國化”“玄奘與唯識學”“玄奘與佛經翻譯”“玄奘慈恩宗的傳播”等六個主題展開討論,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玄奘法師相關各領域研究的最新進展,每篇文章皆有獨特見解,于小組研討中也體現了平等互鑒的大會精神。

北京大學南亞學系教授葉少勇作三組總結。基于玄奘法師帶回的印度原本及其所譯漢文文獻、中土撰述三類文獻,進行義理、哲學研究。多篇文章于西方哲學、中印唯識學比較研究,視野開闊圓融,體現不問東西的學術態度和對印度梵文本重視的進步方向。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曹剛華作四組總結。以“譯經”“思想”“文獻”六字概括四組研討,涵蓋玄奘法師佛學思想、海內外文獻翻譯等方面,于玄奘法師所譯文本研究最為深入。

南京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楊維中作五組總結。以因明學說為特色,提出應重視因明學于東方背景下的還原與詮釋,并于玄奘形象、長安地域文化、唯識學方面進行深入探討,強調玄奘法師的僧人和學者身份。




西安作為玄奘法師譯經弘法的核心之地,不僅留存著大慈恩寺、大雁塔等歷史印記,更以持續的實踐行動推動玄奘法師相關學術的傳承與發展。
設立玄奘研究院,舉行文化節,開展高僧講經、青年學者論壇等活動,將學術研討與社會活動相結合,搭建起傳統與現代對話的橋梁。

近代思想家魯迅先生將玄奘法師譽為“民族脊梁”。這片土地始終承載著對玄奘文化遺產守護與傳承之重任。 此次學術研討會,既是對千年學術傳統的致敬,也是一次承前啟后的創新突破。
昔日玄奘法師在此伏案譯經,用文字架起文明溝通的橋梁;今日學者于此激揚文字,以學術之力延續文化交流的薪火。
中華文明海納百川、開放包容品格,伴隨著文明互鑒的智慧,一直照亮著我們腳下的道路。(視頻/果木 圖片/妙心 果樹 編輯/妙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