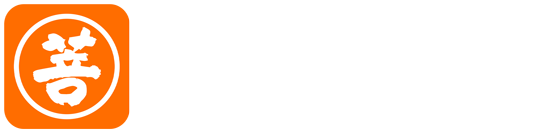法顯大師與荊州天王禪寺的因緣
——兼論荊州市法顯文化促進會成立的現實意義
荊州市法顯紀念館館長 釋恒峰
禹分九州,始有荊州。荊州歷史悠久,底蘊深厚,遍地閃爍著佛教文化的瑰麗光芒。早在1600多年前,西行取經第一人法顯大師在實現西天取經的壯舉后,駐錫荊州辛寺(即今天王禪寺)幾近五年之久,并圓寂于此。在此期間,大師撰寫了歷史巨著《佛國記》,翻譯并講解了多部重要梵文律典,為中國佛教的健康傳承作出了關鍵性貢獻。這不僅極大地豐富了荊州歷史文化的內涵,也奠定了天王禪寺在中國佛教文化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法顯大師西行求法緣起
佛法的住世與弘揚,僧團發揮著根本性的作用,但如果沒有佛陀所制定的戒律的攝持,僧團就不可能穩定地存在,更不可能獲得長久的發展。正如元照律師所說:“佛法二寶,并假僧弘。僧寶所存,非戒不立。”(《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釋序文》)遺憾的是,在此之前,盡管漢地有許多來自西域諸國的僧人翻譯各種各樣的經典,但律典的翻譯卻非常罕見。直到曹魏嘉平二年(公元250年),始有天竺僧人曇摩迦羅翻譯出《僧祇戒心》,漢地才開始有了戒律。但在此之后,對戒律的翻譯仍顯凋零。東晉道安大師因應當時佛教僧團發展的需要,根據戒律的精神及當時僧團的實際狀況,制定了僧尼規范三例作為僧團應遵循的法度。盡管此三例僧尼規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僧團的管理,但對于需要長期穩定發展的中國佛教來說,還是遠遠不夠。缺乏戒律的具體指導,極大地限制了佛教在中國的發展。隨著僧團的發展與壯大,如何對其進行管理,僧人如何共住共修,成為當時中國佛教界迫在眉睫的問題。
法顯大師正是生活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下。據《出三藏記集》卷十五《法顯傳》中記載,大師俗姓龔,平陽郡武陽(今山西省臨汾市,一說山西省襄垣縣)人。兄弟四人,其中三人幼年夭折,父恐“禍殃及顯”,三歲時便把他度為沙彌。父母去世后,便決心出家,二十歲時受比丘戒,正式成為僧團一員。大師“志行明潔,儀軌整肅”,針對當時佛教經典翻譯在戒律方面的缺失,他“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正是這樣一種為佛教擔憂的心情,促使大師發起了西行求法的誓愿。當然,這一求法愿望的萌發,也有其歷史背景。自從西漢張騫出使西域并開辟絲綢之路以后,漢地與西域諸國的交往日益頻繁。當時西域有不少國家已信奉佛教,絲綢之路的開通,為西域僧人進入漢地弘揚佛法提供了便利條件。西域僧人的前來,無形中也激發了漢地僧人對佛教發源地的神往。
種種因緣和合,大師于后秦弘始元年(公元399年),與慧景等四僧結伴,矢志西行求法,途中又遇智嚴等五僧,前后共十人。然而,在隨后漫長而又艱辛的求法歲月中,一同結伴西行的僧人,有的半路而歸,有的客死他鄉,有的留居他國,最后唯有大師一人堅持走完了這條漫漫求法之路。在經歷無數的磨難之后,歷時十四年,大師抄得四部佛教梵文經書《長阿含經》《雜阿含經》《彌沙塞律》《雜藏經》共一百余卷。隨后,他帶著之前于天竺抄得的《摩訶僧祇律》《薩婆多律抄》《大般泥洹經》《摩訶僧祇阿毗曇》等十余部梵文經籍,萬里奔波,歷經驚風險浪,飽受饑渴勞苦,終于在離鄉背井十四年之后,于東晉義熙八年(公元412年)從海路返回祖國,實現了西行求法的誓愿。
二、法顯大師駐錫荊州的歷史因緣
公元416年,法顯大師離開建康(今江蘇南京)來到荊州,既是歷史選擇,也是機緣所致。
1、法顯大師在建康道場寺譯經期間,因有人對譯本的真實性提出質疑而引起紛爭,譯經工作被迫中止,大師只能選擇離開建康,前往別處。
2、北方諸侯奔突,政局動蕩,不利于安心開展譯經工作,這在客觀上促使法顯大師選擇繼續留在政局相對穩定的南方地區。
3、作為海、陸兩路佛教文化交流連接地之一的荊州,在法顯大師駐錫之前就有西來梵僧在此弘法譯經,開始了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活動,為荊州地區佛教的傳播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成為法顯大師晚年駐錫荊州辛寺的重要因緣。
4、荊州辛寺是當時最主要的佛經翻譯道場,律學興盛,翻譯人才眾多。412年,梵僧曇摩耶舍到辛寺翻譯佛經,擅誦毗婆沙律,“披榛而至者三百余人”。413年,精通漢語的卑摩羅叉在辛寺主講《十誦律》(即《薩婆多律抄》,由鳩摩羅什與佛若多羅等于后秦弘始七年譯出),“析文求理者,其聚罽賓僧人如林”,弟子慧猷從之受學,成為荊州地區的律學宗師。辛寺濃厚的律學氛圍和眾多律學人才,正好契合法顯翻譯和傳播律學的需求。
三、法顯大師在荊州的主要弘法活動
法顯大師駐錫荊州辛寺(即今天王禪寺)幾近五年(約公元416——420年),并在此圓寂,享年86歲。法顯大師緣結荊州,主要弘法活動有以下兩個方面。
1、完成了《佛國記》的修訂
關于《佛國記》的付梓地,一度眾說紛紜。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術界一致認為,法顯大師在駐錫荊州辛寺期間,完成了著作《佛國記》的修訂。
《佛國記》又名《法顯行傳》《法顯傳》《歷游天竺紀傳》等,約13980字,系法顯大師唯一的著作。這部著作詳細記錄了法顯大師從長安出發,經西域至天竺的旅行經歷,不僅描述了旅途的艱難和險阻,還詳細記錄了我國西域地區和中亞、南亞、東南亞30多個國家的地理、交通、文化、風俗、物產、社會生活、政治經濟、自然景觀等方面的內容,是研究當時中外交通和中亞、南亞諸國歷史、地理、宗教、文化及社會狀況的重要史料。
《佛國記》屬佛教地志類著作,體裁是一部典型的游記。大師以其生動的筆觸,將旅途的艱辛與發現的喜悅、對佛教的虔誠與對家國的憂慮交織在一起,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佛國記》在世界學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近現代以來,先后被譯成英、法、日等國文字,成為中外史學家、文學家研究的瑰寶。
2、翻譯并宣講多部重要律典
法顯大師駐錫荊州辛寺后,仍積極從事譯經事業。據《天王禪寺功德碑》《皇甲古剎碑》等史料記載,法顯在辛寺參與翻譯的律典共六部七十三卷,并在辛寺、皇甲古剎對其中《摩訶僧祇律》《大般泥洹經》兩部律典進行了講解。
三、法顯大師對荊州佛教文化的影響
法顯大師在荊州辛寺不僅完成了歷史巨著《佛國記》,還翻譯并講解了《摩訶僧祇律》《大般泥洹經》等多部律典,極大地填補了中國佛教戒律殘缺不全的狀況,為隨后南北朝時期佛教走向良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還引發了時人對佛教適應社會發展的思考。大師極力倡導的“涅槃實相”“佛性實有”等理論,與當時廣為流行的般若性空之學相得益彰,與日漸興起的玄學思想相輔相成,故而被當時社會各階層廣泛接受。南朝梁僧祐法師曾指出“法顯后至,泥洹始唱,便謂常住之言,眾理之最,般若宗極,皆出其下。”關中四圣之一道生法師受法顯翻譯的《大般泥洹經》啟發,“唱闡提之人皆當成佛”之說,孤明先發,使涅槃佛性思潮一時競起,為后世禪宗的光大,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對此,近代著名佛教學者湯用彤評價說:“開中國佛理之一派,至為重要。”
在法顯大師的直接或間接影響下,荊州這塊佛教文化發展的良田沃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中外著名高僧和佛教文化學者參與譯經事業,如梵僧佛馱跋陀羅,南朝齊宗室大臣、文學家蕭子良(460—494),荊州名士劉虬(437—495),《須大孥經》翻譯者法堅大師等。唐貞觀三年(629),著名高僧玄奘法師西行求法之前,從四川乘船來到荊州辛寺講經弘法,先后講解《攝大乘論》和《解深密經》,荊州僧俗四眾,包括當時鎮守荊州的漢陽王也前往聽講,“其中有深悟者悲不自勝”,講完之后“?施如山(施舍的財物堆積如山)”。史料記載,玄奘法師駐錫荊州辛寺達一年零三個月之久(公元629年5月至630年8月),對荊州佛教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
據文獻考證,在法顯大師之后約1200年間,先后有七十多位中外著名僧俗翻譯家追尋大師的足跡來到荊州辛寺從事譯經事業。在此期間,盡管“辛寺”名稱歷經多次演變,但它作為全國最大佛經譯場的地位一直沒有改變,作為全國佛教文化中心的地位一直沒有改變,這不僅極大地豐富了荊州歷史文化的內涵,也奠定了這座千年古剎在湖北乃至中國佛教發展史上極其重要的地位。
四、法顯文化的重要載體——荊州天王禪寺
荊州天王禪寺自東漢建寧元年(公元168年)恒印祖師開山以來,卓然存續1800多年,歷經三次易址,四次更名,演進之跡歷歷可考,古跡文史斑斑可證。在以法顯大師、玄奘大師等為主要代表的歷代高僧大德的加持下,佛教文化雨澤信眾,佛理經典翻譯傳播,寺院戒律莊嚴道場,佛教遺產有序傳承,法脈汲深流遠,法泉清粹不涅,于涵泳沉潛、佛理宣化闡揚中,佛子龍象輩出,經集匯聚如海,在佛教中國化的歷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因荊州古城老南門外御路口擴建施工,考古人員對辛寺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出土石碑三通,分別為“辛寺中興功德碑”“天皇道悟禪師傳法碑”“天王禪寺功德碑”,分屬東晉、李唐、明初三個朝代。碑體破損嚴重,大片殘缺,但碑文猶可辨析。其中《辛寺中興功德碑》立于公元422年(即法顯大師圓寂荊州辛寺后第二年),碑載“□顯法師駐錫辛寺,續著佛國記,終付梓。皆西竺□□也,時□相傳閱。”為佐證法顯大師在荊州辛寺完成《佛國記》的修訂,提供了寶貴的實物史料。
以上三通石碑碑文顯示,荊州辛寺自公元168年恒印祖師開山以來,歷經三次易址,四次更名。

天王禪寺歷代中興祖師
恒印(公元146——?年),天王禪寺開山祖師。荊州孱陵(今公安縣)文氏子,父母早亡,年十六立出塵之志。二十一歲于澧州(今湖南津市)古大同寺禮真一和尚圓具,次年托缽至江陵草市,因感悟“此乃靈異之地”,遂“卓錫振地,結茅而居”,取名“辛寺”。公元184年,荊州刺史王睿捐資大修辛寺,寺院規模日漸宏大,史載“為殿者九,為樓者十八,凡三千六百僧舍,望風投奔者不絕于途”。
法顯(公元334——420年),俗姓龔,平陽郡武陽(今山西臨汾)人。三歲度為沙彌,二十歲圓具。公元399年,師“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不顧六十五歲高齡,毅然西行求法,歷時十四載,游歷三十余國,取回經律十余部。師八十二歲駐錫天王禪寺,翻譯《摩訶僧祇律》《大般泥洹經》等律典,講集之余,完成著作《佛國記》的修訂。八十六歲圓寂于此。
玄奘(公元602——664年),中國漢傳佛教四大佛經翻譯家之一,唯識宗創始人。唐貞觀三年(629)5月,師駐錫天王禪寺,講解《攝大乘論》和《阿毗達摩》等經典,荊州僧俗四眾“有深悟者悲不自勝”。因受法顯精神感召,師于公元630年8月,在天王禪寺“具齋立誓”,開啟漫漫西行求法之旅。
道悟(公元748——807年),即天皇道悟禪師,唐代禪僧,婺州東陽(今屬浙江)人,俗姓張。年二十五依杭州竹林寺具戒后,謁徑山國一,服侍五年,終受印可。建中二年(781),入衡岳參石頭希遷禪師。初住灃陽,后棲止當陽紫云山。建中四年(783)駐錫荊州天皇寺,精修梵行,為江陵尹右仆射斐休所歸崇,法席愈盛,世稱天皇門風。
道悟(737——818),即天王道悟禪師,渚宮(湖北江陵)人,俗姓崔。十五歲依長沙寺曇翥和尚剃度出家,二十三歲參嵩山律德,尋參石頭希遷,止二年,但不契悟,遂入長安參南陽慧忠,更謁馬祖道一,言下大悟,且依其勸說,還至渚宮。師于元和二年(807)駐錫天王禪寺,至元和十三年(818)四月示寂,世壽八十二春,僧臘五十八夏。
峰偉(1301——1374),濠州鐘離(今安徽鳳陽)人,俗姓朱。十三歲于九華山甘露寺祝發,十六歲圓具。明洪武二年(1369),師駐錫荊州天王寺,因講解《大乘起信論》《六祖壇經》等經典,深得荊州藩王朱柏贊許。次年,朱柏奏請父皇朱元璋撥專款整飭天王寺,獲準。是年夏,朱元璋御賜“護國寺”金匾,并“就地充田九十九公頃”。乘此因緣,師大興土木,寺院規模“遠超往昔”。
五、法顯文化的精神內涵及當代價值
法顯大師是中國最早具有世界眼光和開創中國佛教對外友好交流事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足跡遍及當時西域諸國、印度諸國、斯里蘭卡和印度尼西亞等國,搭建了一個中外溝通的橋梁,堪稱“一帶一路”的先行者;大師秉承好學敏思、廣識博聞的中華傳統,所到之處,不但認真學習當地語言,而且細心觀察當地民俗、文化和社會,撰寫了歷史巨著《佛國記》,堪稱中外文化交流的先驅者。
法顯大師駐錫荊州,是荊州乃至中國佛教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大師堅定不移的信念、救度蒼生的慈悲、堅忍不拔的毅力、百折不回的意志、孜孜不倦的進取、深厚真摯的情義、心系桑梓的情懷、舍死忘生的胸襟,賦予了荊州歷史文化深厚的底蘊,不僅豐富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內涵,而且成為中華民族奮斗精神的一種象征,對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都起著重大的激勵作用,具有不可估量的現實價值。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在重大國際外交場合先后八次提及“高僧法顯”,習主席頻頻為“高僧法顯”點贊,令人鼓舞。荊州佛教歷史悠久,文化積淀深厚,法顯大師及天王禪寺已成為荊州人文歷史的一個文化符號。法顯大師的精神品質,已深深嵌入荊州歷史文化的肌理,凝聚起荊州兒女篳路藍縷、團結奮進的強大精神力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深入挖掘、有效保護、傳承利用好這一具有荊楚文化特色的歷史文化資源,從不同維度探討“佛教中國化”這一時代命題,進一步推動佛教中國化“荊州實踐”走深走實,加快推動天王禪寺的建設,是擺在荊州佛教界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2024年11月18日,在荊州市有關部門的支持下,荊州市法顯文化促進會正式成立,這是法顯大師與荊州千年佛緣的延續,是荊州乃至湖北佛教文化史上的又一大事因緣。與會專家學者一致認為,法顯大師所開創的西行求法運動延續千余年之久,對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荊州,不僅是法顯大師的圓寂地,更是法顯大師譯經、講學、著述的重要駐錫地,荊州成立“法顯文化促進會”,研究、繼承、弘揚以法顯大師為代表的一大批中外求法僧不畏艱險,開拓進取的精神,既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又有巨大的現實意義。

2024年11月18日,荊州市法顯文化促進會成立。

荊州市法顯文化促進會第一屆理事會聘請湖北省佛教協會常務副會長隆醒法師(右二)、荊州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孫賢坤(左二)、華南農業大學人文與法學學院博士生導師何方耀教授(右一)、荊州市佛教協會會長心繼法師(左一)為名譽會長。
首先,在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新時代,任何地方的發展都被納入全球發展的潮流之中,必須以開放的胸襟面向世界大勢,適應世界潮流。而法顯大師作為西行求法運動“創辟荒途”的開拓者,其不畏艱險、舍身求法的壯舉,其敢于探索未知領域,放眼世界的偉大胸襟,正是我們今天面對世界一體化潮流所需要的重要精神財富。
其次,在人工智能飛速發展的今天,社會各行各業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只有勇敢地探索未知領域,不斷地創新,才能贏得發展的機遇,而法顯大師等一大批西行求法的先行者,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創新思維,敢于挑戰未知領域,這種寶貴的精神品質,正是當下人工智能時代所需要的精神和勇氣。
第三,繼承優秀文化傳統,建立文化自信。荊州本是楚國故都,文化歷史源遠流長,佛教文化就是其中之一。以法顯大師為代表的佛教界精英從魏晉以來,在與印度等西域各國的交流中,不斷吸收外來文化,將印度的佛教改造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漢傳佛教文化,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禪宗,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傳承體系。成立荊州市法顯文化促進會,就是要推動對傳統優秀佛教文化的發掘、整理、繼承、創新,為建立新時代的文化自信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撐和歷史借鑒。

荊州市佛教協會副會長、荊州市法顯文化促進會主要發起人、荊州市法顯紀念館館長、荊州天王禪寺住持恒峰法師講話。
 荊州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市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主任楊清亮講話。
荊州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市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主任楊清亮講話。

華南農業大學人文與法學學院博士生導師何方耀教授代表與會專家學者發表主旨演講。
作為法顯文化的重要載體,荊州天王禪寺將緊緊依靠當地黨委政府,加快推進易址規劃重建步伐,以“文化興教,文化興寺”的理念,將天王禪寺建設成為一座既有濃厚佛教氣氛,又有豐富文化內涵;既有純正道風,又有嚴謹學風;既能安僧辦道,又能對外弘法;既繼承傳統,又適應現代的都市叢林。同時,天王禪寺將充分依托荊州市法顯文化促進會這一平臺,團結帶領廣大信眾,深入學習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宗教中國化的重要講話精神,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為指引,積極響應國家強盛、民族復興偉大時代的召喚,進一步發揮佛教在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服務“一帶一路”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弘揚法顯精神,傳承法顯文化,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動扛起佛教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大旗,把天王禪寺打造成為法顯文化權威闡釋地、活動聚集地、場景再現地、文旅目的地,在荊州全力建設江漢平原高質量發展示范區的征途上,展現天王禪寺與時代同愿同行的美好愿景。(圖/文來源于荊州天王禪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