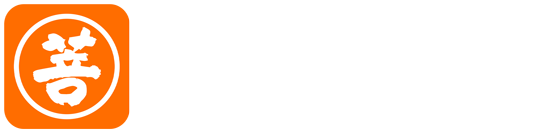(本文作者:了成法師,紹興市佛教協會副會長、越城區佛教協會會長、龍華寺方丈)
20余年前,即公元2000年,是個特別的年代,彼時,中國加入WTO在望,互聯網剛剛興起,手機還是稀罕物,世紀之交的千禧年,人們迫不及待地擁抱嶄新的自己,期望事業有成,家庭幸福,而我卻離家別女,一個人背上行囊,邁著沉重腳步,步入重慶佛學院……
閱讀“崇佛大事記”
特殊年代留有特殊記憶。我原籍浙江寧海,1968年10月出生,1989年,高校畢業后順利進入公安系統工作,不久調到上海。一次,與朋友一起上街,一位看相的叫住了我。先生看了一會告訴我:“你眼前這碗飯是吃不長久的。如果你要做下去,要么有牢獄之災,要么壽命不長。”我當時聽了付之一笑,根本沒放在心上,雖然說家里人也崇佛,但從來沒有出家的念頭,然后一系列的事情出現,讓自己不得不相信,自己的命里注定要出家的。
我1991年結婚,結婚后才慢慢出現諸多的不和諧,于是選擇了離婚,女兒歸前妻撫養。1997年離婚后我非常茫然,一度憤世嫉俗樣子,自然地想到了出家。

2000年9月,我徑直去重慶佛學院高級班就讀。重慶佛學院是經國家宗教事務局批準的漢語系高級佛學院,實行“學修一體化、生活叢林化”辦學方針,實行供給制,除供給學習和生活用品外,還發給助學金,優秀學生還有獎學金。學院是清靜,但有嚴格戒律。就是因為戒律使我焦噪的心漸漸平靜下來,兩年中我學習了沙彌律、佛教概論、佛教概觀、中國佛教史、印度佛教史,還有政治、古文、現代漢語、中國古代史和書法繪畫等。平時還去華巖寺實習,聽佛學講座,參禪、打坐等。兩年的學習是短暫的,但收獲與人為善、團隊合作、堅韌、自律等寶貴品質卻是長期的。
2002年的春天,我輾轉來到紹興市柯橋區的柯城寺,恰好寺院在筑大殿,住持讓我幫著干活。我原先有嚴重的胃病,出家前曾四次胃出血,不能吃筍之類食物,而紹興春天的筍,是寺院里"長和飯",每次吃了筍后,胃部十分難受,心里竟然冒出一個“不要做和尚”的念頭來。寺院一位老居士了解我的想法后,勸我:出家的事不能悔的,你可在佛前求一求,如果自己決心出家,能否讓佛菩薩治好自己的胃病。我一聽,覺得蠻有道理,依計而行,在佛前虔誠跪告,求畢,奇跡出現了,剛才還胃如刀絞,竟然全身舒服。我喜出望外,堅信佛菩薩在護佑我,從此我堅定走上崇佛之路。
2002年冬天,我告別柯城寺,來到了爐峰禪寺。皈依于凈芳大和尚座下。從此,獲得明師教誨,方向陡明,智慧大增,弘法精進。至2005年,短短三年時間,我從一名普通的大殿香燈小沙彌很快做到僧值,再升到知客。恩師知遇栽培之恩,終身難忘。
2006年,我在寧波雪竇山求得三壇大戒。依初壇、二壇與三壇正授,分別得到沙彌戒、具足戒、菩薩戒的戒體。這是我從崇佛之路到護法之路轉折點。

翻開“龍華寺記事簿”
進入新世紀,古城紹興更加重視保護歷史街區,2004年底,市政府開始對八字橋歷史文化街區開展保護整合工作。具有1500余年歷史的龍華寺自然列入重建修繕對象。
2005年9月,市政府將龍華寺的管理權交給市佛教協會。
2006年春天格外美好。我被市佛教協會委派到紹興市區龍華寺做監院。其時修繕工程竣工,有大雄寶殿、天王殿及西廂房等占地面積達4500平方米,建筑面積為1500平方米,寺前建有牌坊一座,上鐫“龍華證道”“南朝古剎”,時為紹興市區最莊嚴的寺院。
我深感責任重大,使命在肩。不斷加強學習、修養,拜名師、求“真經”,充實完善自己。2009年依新昌大佛寺方丈傳實,求受法脈;2016依爐峰禪寺方丈凈芳接法; 2016年蒙圣輝長老垂愛,于湖南長沙麓山寺求得禪門臨濟正宗法脈,有幸成為第42世法嗣。進入法門以來,得以親近多位名師,言傳身教,耳提面命,醍醐灌頂,得益匪淺。特別榮幸的是,我于2012年被任命為紹興市佛教協會副會長,2014年10月起兼任越城區佛教協會會長,2013年,就讀人民大學哲學院宗教系佛教文化專業碩士研究生班至結業。

2016年10月15日,紹興市越城區龍華舉行開放十周年暨寺了大雄寶殿五百羅漢圣像開光慶典,借此勝緣,我經省佛教協會批復榮膺方丈,如法舉行了升座法會。
在黨和政府的悉心培養下,我先后當選紹興市政協第六、七、八、九屆委員;紹興市佛教協會第五、六、七屆副會長,越城區佛教協會第三、四、五屆會長,浙江省佛協第七屆、八屆理事。縱覽“龍華寺記事簿”,取得成績歷歷在目:
20年來,殫精竭慮建道場。涅槃重生,舊貌變新顏,參照伽藍布局,在寸土寸金的八字橋歷史街區依次擴建大雄寶殿,續建世界和平吉祥寶塔、藏經樓、東西廂房、弘法樓、尚書房等,目前寺院占地20余畝,建筑面積達近8000平方米。廣寧橋畔,古運河邊,國土莊嚴,典雅秀撥,成為歷史文化街區一顆耀眼明珠。
20年來,如威如儀弘法事。龍華寺依照佛教儀軌,紹隆佛種,續佛慧命,舉辦各類莊嚴佛法、為眾生消災避難的祝福活動,主要有水陸、佛誕、經讖、普佛、盂蘭盆、焰口、開光、升座、祈福法會等。20年來,共進行各類佛事活動4000余堂,香客共參與126862人次。廣作佛事度有緣,道場中興為越中。龍華寺已成為古城集禮佛、旅游、文化于一體的莊嚴道場。
20年來,因事制宜巧管理。龍華寺從初創始,就建立規范叢林制度,建有僧眾誦經、清修、佛事等活動清規;同時也建有現代財務、后勤管理,僧人生活、違犯處罰等具有叢林和現代共有方式。車輛、消防、及僧人醫保、社保實等實施社會化管理。2020年,龍華寺還實施標準化管理,創新寺廟管理新形式,制定5大方面管理標準42項,影響浙江叢林。寺院也因此獲得許多殊榮:第三屆平安場所創建全國先進,浙江省民族團結進步示范點,浙江省消防工作先進集體、浙江省普法工作示范點。被省市區評為和諧(平安)宗教場所。

20年來,文化潤教出新果。多年來,龍華寺致力于佛教文化弘揚,踐行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人間佛教思想。創設龍華佛學圖書館、開設越州講壇——龍華證道佛學專題講座、成立龍華慧成書畫院、編纂出版《龍華寺志》等,為弘揚紹興佛教文化事業長期努力,目前寺院已成為古城接受傳統文化的好去處。
20年來,公益慈善貫春秋。扶貧、賑災救難、公益慈善是新時期佛教寺院為政府分憂助力點。一直以來,龍華寺以“黨和政府所關心、社會各界所關注、困難群眾所需要”為宗旨,應時應事,資助患病貧困兒童,救助低收入家庭,幫助改善貧困地區教育條件,助力脫貧攻堅,應急救災等,服務社會、利濟眾生,累計捐款達110余萬元。

20年來,對外交往樹法幢。隨著龍華寺全面修復,法會昌盛,許多與龍華寺有過佛緣交往的僧尼和友好人士,紛紛遠涉重洋,來寺禮佛進香,參觀旅游,寺院先后接待了日本、澳大利亞、韓國、新加坡等國家僧俗賓客;寺院也主動走出去,幾次遠赴日本,澳大利亞開展佛學、茶道等文化交流,舉行“紹興緣一一中日茶禪書文展”;2019年5月,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成功訪問寺院,古寺、古城之美,已深深成為他的記憶。
20年來,龍華寺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我也從一名普通的僧人逐步成長為佛教寺院、宗教團體的一名負責人,成為省、市、區宗教界的代表人士,我發自內心的最大感恩:感恩黨和政府的關愛支持,感恩諸佛菩薩的慈悲加持,感恩出家僧眾的一心住持,感恩檀越善信的虔心護持。
書寫“弘法利生新篇章”
我已步入花甲之年,在有生之年,要發揚法藏比丘不達目標,誓不罷休勇猛精進的菩薩精神,踐行佛陀“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利眾情懷,率領正信的佛門弟子,發揮佛教優勢,促進民族和睦,宗教和順,社會和諧,世界和平,助力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佛教在中國長期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三大優良傳統,即講經論道、農禪并重和對外交流。發揚并繼承這些傳統將是我余生堅持。
堅持“講經論道”
我國歷代高僧所翻譯的佛經和撰寫的佛教著作,為我們留下了極為珍貴的文化遺產。佛教徒不應只關心自己的修行,而是要關心現世人間。佛教的出世思想不是躲在深山叢林中,藏在伽藍殿宇里,而是在五欲六塵之中尋求解脫和自在的人間生活,這才是出世與入世的融合,也是佛陀傳播人間佛教的初衷。龍華證道未來應重視教育、文化、藝術、音樂、學術和資訊的發展,擴大國內外佛教人士的參與,注重傳統與現代相結合、本土化與國際化的融合,深化信仰,服務眾生。
堅持“農禪并重”
趙樸初老居士曾說過:“農禪并重”從廣義上理解,“農”系指有益于社會的生產和服務性勞動,“禪”系指宗教修學,兩者不可偏廢。我們作為新時代佛教徒,在進行宗教學修的同時,也要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積極參加生產勞動和其它為國家建設事業服務實踐。
堅持“對外交流”
“走出去”,增進文明互鑒,向世界講好紹興佛教故事。交流主導人類未來發展方向,佛教的發展基因、主線和趨勢都離不開交流,當佛教文化以廣闊視野融入整個地球時,地球可以成為一個充滿愛和喜悅的村莊。只有在文化交流的融合和共識下,人類和平與和諧發展才有可能實現。紹興歷史上是東南佛國,漢傳佛教祖庭多、祖師多、僧人多、信眾多,傳承至國外的法脈、戒脈多,與日、韓佛教在法緣、法誼、法情上密切。紹興佛教要走出國門,走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展現中國氣派,服務中外文明互鑒。
加強教風建設,培養新時代佛教事業優秀接班人。宗教團體的自身建設與教職人員的素質建設,事關中國佛教繼承、發展和創新,作為一名佛教團體負責人,在加強全面從嚴治教同時,要加強自我學習、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監督;“崇儉戒奢”,秉持勤儉儉樸理念,杜絕講排場、比闊氣、貪圖享樂行為,自覺帶頭精進修學、正本清源,守持戒律,以自身正為廣大教職人員和信教群眾作出從嚴治教的典范。

龍華寺,我的根,我的道場,我傳承法脈。根據《龍華寺志》編撰過程中,挖掘出的優秀歷史文化內涵,我將不遺余力繼承、恢復、發展,以莊嚴道場,弘法利生。
光陰荏苒,歲月不居。太陽有時會被遮擋,但從未停止發光,正如我們一刻不停走在路上,雖有萬般紛擾。繼續背起行囊,放下過往,一路向前,命運將擁抱每一個無畏前路的修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