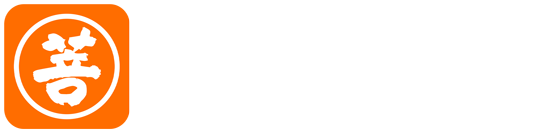《華嚴(yán)字母》誕生的歷史非常悠久,具體的產(chǎn)生年代已經(jīng)沒(méi)有詳細(xì)的文獻(xiàn)資料能夠考證,但是據(jù)說(shuō)是古印度時(shí)期佛陀釋迦摩尼講經(jīng)時(shí)所使用語(yǔ)言的字母,共有四十二個(gè)。由于四十二個(gè)字母完整的出現(xiàn)在《華嚴(yán)經(jīng)》的《入法界品》這一品中,因此被稱(chēng)為《華嚴(yán)字母》。?
至于佛陀講經(jīng)時(shí)使用的是何種語(yǔ)言,現(xiàn)在多位著名學(xué)者已經(jīng)考證出了明確的結(jié)果,通常認(rèn)為是古印度的巴利文。如季羨林先生在他所著的學(xué)術(shù)論文《原始佛教語(yǔ)言問(wèn)題》中有著明確的的考證:“據(jù)錫蘭佛教徒的傳說(shuō),現(xiàn)存的巴利文<大藏經(jīng)>就是摩哂陀(阿育王的弟弟,一說(shuō)是他的兒子)帶到錫蘭去的,而巴利文也就是摩揭陀語(yǔ),換一句話(huà)說(shuō),巴利文就是佛所說(shuō)的話(huà),而巴利文<大藏經(jīng)>也就是佛教的唯一正統(tǒng)的經(jīng)典”。從上面這段話(huà)中可以看出,季羨林先生明確指出了佛陀講經(jīng)時(shí)用的是巴利文,也就是說(shuō)佛經(jīng)的最初傳播時(shí)用的也是巴利文。
再如周有光先生在《世界文字發(fā)展史》中寫(xiě)到:“佛陀釋迦牟尼自己在公元前6世紀(jì)傳教用的語(yǔ)言,是佛教圣地摩羯陀的俗語(yǔ)。這種俗語(yǔ),經(jīng)過(guò)佛教經(jīng)典的洗煉,成為佛教的神圣文字'巴利文'。阿育王提倡佛教,俗語(yǔ)文字在阿育王時(shí)代的勢(shì)力蓋過(guò)了梵文。”季羨林先生在《原始佛教語(yǔ)言問(wèn)題》一文中也特別強(qiáng)調(diào)了 “早期佛教使用的語(yǔ)言不是梵文而是巴利文。”可見(jiàn)釋慧皎法師在《高僧傳》所說(shuō)的“自大教?hào)|流,乃譯文者眾,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復(fù),漢語(yǔ)單奇”這段文字中的“梵音”是對(duì)古印度語(yǔ)言的泛指,這完全可能是古時(shí)信息交流通匯不像今天這樣便利,古人還沒(méi)有能力對(duì)古印度國(guó)度中的各種不同的語(yǔ)言作嚴(yán)格的區(qū)分。由此可見(jiàn),《華嚴(yán)經(jīng)·入法界品》中記載的四十二個(gè)字母即“華嚴(yán)字母”為古印度巴利文的拼音。?
《大方廣佛華嚴(yán)經(jīng)》就是漢傳佛教翻譯的經(jīng)典中重要的一部,其篇幅非常龐大。現(xiàn)在我國(guó)漢傳佛教中的《華嚴(yán)經(jīng)》是由古代高僧翻譯的漢語(yǔ)版本,常見(jiàn)的有三個(gè)版本即:晉譯華嚴(yán)——東晉安帝義熙十四年(公元 418)佛陀跋陀羅首譯《華嚴(yán)經(jīng)》五十卷(后開(kāi)作六十卷);唐譯華嚴(yán)——唐武后證圣元年(公元695)于闐實(shí)叉難陀奉詔再次翻譯,歷時(shí)五年翻譯了《華嚴(yán)經(jīng)》八十卷,三十九品;唐德宗貞元十一年(公元 795)般若三藏所譯的《大方廣佛華嚴(yán)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愿品》,相當(dāng)于八十華嚴(yán)《入法界品》,后稱(chēng)為四十華嚴(yán)。
據(jù)史料記載,由于造紙與印刷技術(shù)還沒(méi)有發(fā)明,因此古印度時(shí)期佛經(jīng)是記錄在“貝葉”上的,這是一種植物的葉子。可見(jiàn)當(dāng)時(shí)的文字的記錄方式與保存都是非常不易,因此當(dāng)篇幅龐大的《華嚴(yán)經(jīng)》在向東方傳播的過(guò)程中,有所遺失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從東晉時(shí)期傳入中國(guó)的“四十華嚴(yán)”與唐代時(shí)期傳入的“八十華嚴(yán)”并非完整。唐代的后期,烏茶國(guó)進(jìn)貢時(shí)又帶來(lái)了《大方廣佛華嚴(yán)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愿品》,也就是通常所說(shuō)的“四十華嚴(yán)”。“四十華嚴(yán)”的內(nèi)容只有《華嚴(yán)經(jīng)》中的“入法界品”,但是與“八十華嚴(yán)”的“入法界品”相比,“四十華嚴(yán)”的內(nèi)較為完整。著名的高僧弘一法師(李叔同)在研究了《華嚴(yán)經(jīng)》的這三個(gè)不同版本之后認(rèn)為,“四十華嚴(yán)”的內(nèi)容補(bǔ)充了“八十華嚴(yán)”中“入法界品”的不完整,因此他建議在誦讀完“八十華嚴(yán)”的第 59 卷后接讀“四十華嚴(yán)”,這樣共誦讀 99 卷,后被稱(chēng)為“一百華嚴(yán)”。弘一法師的建議彌補(bǔ)了傳入中國(guó)三個(gè)版本《華嚴(yán)經(jīng)》在流傳過(guò)程中所遺失的內(nèi)容。?
江蘇揚(yáng)州高旻寺的“華嚴(yán)法會(huì)”誦讀就是“一百華嚴(yán)”,因此高旻寺舉行的華嚴(yán)法會(huì)所用的時(shí)間較長(zhǎng),法會(huì)的規(guī)模也較其他寺院大,通常需要二十五天左右。在高旻寺每年舉行“華嚴(yán)法會(huì)” 時(shí)期國(guó)內(nèi)外其他寺院都會(huì)有僧侶參加。由此而見(jiàn),高旻寺華嚴(yán)法會(huì)上演唱的“華嚴(yán)字母”在國(guó)內(nèi)具有相當(dāng)大的影響。(節(jié)選自:徐菲 論中國(guó)漢傳佛教梵唄“華嚴(yán)字母”的音樂(lè)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