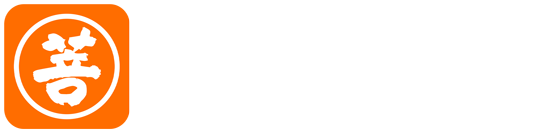自古以來有許多的文史資料中都談到佛教音樂華化的問題,也有許多的學(xué)者都談到佛教音樂華化的開端“漁山梵唄”的真?zhèn)螁栴},以及佛教音樂經(jīng)過魏晉南北朝的發(fā)展,至唐代時(shí)佛教音樂徹底華化。
中國(guó)的佛教音樂及梵唄的根源來自古代印度,在許多佛教經(jīng)典中多有描述佛教音樂在印度非常盛行,如(梁)慧皎《高僧傳·鳩摩羅什》載:“天竺國(guó)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弦為善。凡覲國(guó)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贊為貴, 經(jīng)中偈頌,皆其式也。”這段話是著名的譯經(jīng)家,中國(guó)大乘佛法的傳播者,天竺國(guó)的鳩摩羅什(343-413 年)對(duì)其門下弟子僧睿說的一段話,說明了古印度的傳統(tǒng)是非常看重禮儀的,禮儀中的辭文韻律,都要能夠用音樂來伴奏。國(guó)王接見人民時(shí)必須用歌聲贊頌國(guó)王的品德;禮拜佛時(shí)的一切活動(dòng), 同樣用歌聲來贊嘆佛德為最好的形式。佛經(jīng)中的偈頌,都是繼承了這種傳統(tǒng)方式。
當(dāng)佛教傳入中國(guó)后,這些佛教傳統(tǒng)儀式中各種贊詠的梵唄也應(yīng)該隨之傳入中國(guó),但是,由于語言的問題而無法被中國(guó)人接受而流傳,如梁朝會(huì)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497-554 年) 撰《高僧傳》中云:“自大教?hào)|流,乃譯文者眾,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復(fù),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zhǎng)。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這是一段被引用說明佛教音樂華化困難之處,也是廣泛地被引用的一段話,從這段話中可以說明:佛教傳入中國(guó)后佛經(jīng)的翻譯非常廣泛,卓有成就。
但是佛教中的音聲、梵唄或贊詠傳播得很少。其原因是梵文的讀音是許多個(gè)音素表示一個(gè)字,因此這個(gè)字的讀音中有高低抑揚(yáng)的成分;而漢語大多是一個(gè)讀音就是一個(gè)字。如果用印度音樂曲調(diào)填寫漢語來歌詠贊嘆,則曲調(diào)長(zhǎng)而歌辭短,即曲長(zhǎng)字少,詞曲無法配合;如果用梵語填寫中國(guó)曲調(diào),則梵文構(gòu)詞繁復(fù),中國(guó)曲調(diào)短,即曲短字多,詞曲無法協(xié)調(diào),因此,佛經(jīng)翻譯順利而梵唄一直沒有傳播。
其實(shí)之所以梵唄沒有在中國(guó)傳播擴(kuò)大是因?yàn)檎Z言性質(zhì)的不同,即梵漢不能對(duì)譯。直至“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jīng)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漁山之神制。于是刪治《瑞應(yīng)》、《本起》,以為學(xué)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余,在契則四十有二。其后帛橋,支籥亦云祖述陳思,而愛好通靈,別感神制,裁變古聲,所存止一十而已。至石勒建平中,有天神降于安邑廳事,諷詠經(jīng)音,七日乃絕。時(shí)有傳者,并皆訛廢。逮宋齊之間,有曇遷、僧辯、太傅、文宣等,并殷勤嗟詠,曲意音律撰集異同,斟酌料例。存做舊法,正可三百余聲。自茲厥后,聲多散落,人人致意,補(bǔ)綴不同。所以師師異法,家家各制。皆由昧乎聲旨,莫以裁正。”③文中說明關(guān)于魏陳思王曹植依佛經(jīng)《太子瑞應(yīng)經(jīng)本起經(jīng)》中的內(nèi)容,用中國(guó)語言創(chuàng)制了“漁山梵唄”,這是印度佛教音聲、梵唄華化的開始,從此后的高僧、帝王紛紛模仿“漁山梵唄”用漢語而創(chuàng)制各種佛教梵唄贊詠。
“漁山梵唄”象征著印度佛教音樂在中國(guó)華化的開端,對(duì)于這一問題眾說紛紜,有人認(rèn)為是真,有學(xué)者認(rèn)為是一個(gè)傳說。“漁山梵唄”的曲調(diào)、旋律、歌辭特征是何種情況,現(xiàn)在已不得而知,但是中國(guó)佛教中保存了較多的傳統(tǒng)梵唄既然都是歷史中華化的梵唄,就有其梵唄的共同特征。(節(jié)選自: 傅暮蓉 中國(guó)音樂(季刊)2012年第3期)